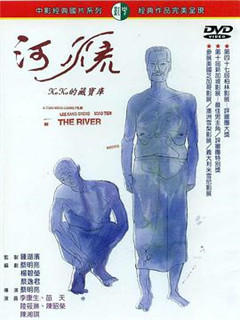- [ 免費 ] 第1章 河與沙漠
- [ 免費 ] 第2章 母親的不適
- [ 免費 ] 第3章 新的壹天
- [ 免費 ] 第4章 調查
- [ 免費 ] 第5章 壞消息
- [ 免費 ] 第6章 草原上
- [ 免費 ] 第7章 水文站
- [ 免費 ] 第8章 陸伯伯
- [ 免費 ] 第9章 水
- [ 免費 ] 第10章 新聞人物
- [ 免費 ] 第11章
- [ 免費 ] 第12章
- [ 免費 ] 第13章
- [ 免費 ] 第14章
- [ 免費 ] 第15章
- [ 免費 ] 第16章
- [ 免費 ] 第17章
- [ 免費 ] 第18章
- [ 免費 ] 第19章
- [ 免費 ] 第20章
- [ 免費 ] 第21章
- [ 免費 ] 第22章
- [ 免費 ] 第23章
- [ 免費 ] 第24章
- [ 免費 ] 第25章
- [ 免費 ] 第26章
- [ 免費 ] 第27章
- [ 免費 ] 第28章
- [ 免費 ] 第29章
- [ 免費 ] 第30章
- [ 免費 ] 第31章
- [ 免費 ] 第32章
- [ 免費 ] 第33章
- [ 免費 ] 第34章
- [ 免費 ] 第35章
- [ 免費 ] 第36章
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AA+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
简
第9章 水
2018-9-27 20:33
夕陽西下,太陽把最後壹抹光輝潑灑在祁連大地上,蒼蒼茫茫的祁連山,此時呈現出靜態的壯美。吳天亮忽然有種窒息感,這是從政以來很少有的感覺,他知道,自己是被這座山壓住了,被這條河壓住了,沒有力量去做翻身的事。
上遊堅決不放水,弄得上下遊關系越來越緊張,市裏眾說紛紜,圍繞著這條河,圍繞著流域,大家各執壹詞,意見壹時很難統壹。吳天亮又不敢強行責令上遊谷川開閘放水,怕將矛盾進壹步激化。
但是水的問題不解決,他這個市委書記就別想當安穩。
下班時間早已過了,吳天亮還在辦公室煎熬著,他在等流域管理處處長鄧家英。吳天亮早年在管理處做過處長,後來到市裏擔任領導,兩年前他就任市委書記,將鄧家英硬性安排在這個職位上,目的就是期望鄧家英勵精圖治,能把流域這盤死棋下成活棋。可事實表明,到現在為止,流域這盤棋還是下不活,非但下不活,而且眼看著下不下去了。
時間壹分壹秒過去,大樓裏壹片安靜,說好七點二十在他辦公室見,現在兩個小時過去了,還不見鄧家英人影。困在辦公室的吳天亮心裏很不是滋味。要說市委書記讓壹個下屬來見他,簡直就是不張嘴都能做到的事,哪還用得著焦灼地去等。可鄧家英這個下屬實在不同,她不但讓吳天亮等,還讓吳天亮等得心裏生煙,等得想發火又發不出來。那天吳天亮在會上動議,試圖用高壓政策,強行從上遊谷川調水,以解下遊沙湖燃眉之急,遭到了鄧家英等人的強烈反對。鄧家英竟然當著那麽多人面,說他不顧自然規律,為了政績,壹次次人為地加劇河的悲劇。氣得吳天亮差點摔了杯子。鄧家英竟不依不饒,又跟他算起了移民賬,算起了下遊打井開荒的賬。移民和打井開荒都是吳天亮上任後谷水市推出的新政,鄧家英這樣做,等於是在攻擊他。吳天亮忍無可忍,厲聲批評了鄧家英壹通,沒想到鄧家英當場提出辭職,說不幹了,退休回家!
娘的,都是沖我撒脾氣!吳天亮罵壹聲,擡起手腕看表,九點過壹刻。他跟自己說,再等十分鐘,要是還不來,就同意她的辭職要求,想幹嘛幹嘛去!這樣下去絕不是法子,都跟他撂挑子,關鍵時刻壹個也指靠不住,這書記還怎麽當,流域還怎麽治理?
十分鐘很快過去了,樓裏照樣沒有動靜。吳天亮脾氣越發大,抓起電話打給秘書:“我讓妳催她怎麽催得到現在還不見影?”秘書嘟囔了幾聲,從對面那扇門裏走過來,小心翼翼地說:“壹小時前鄧處長電話還通著,現在怎麽也打不通。”
“打不通派車去找啊,難道讓我親自去找她?”吳天亮惱了。豈料十分鐘後,秘書慌慌張張跑進來說:“不好了,鄧處長昏倒在路上,目前正在醫院搶救。”
“什麽?”吳天亮大驚失色,等問明情況,馬上驅車往醫院趕。路上他將電話打給路波,質問怎麽回事?路波吞吞吐吐,不肯說實話。吳天亮更是壓不住火,罵路波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廢物壹個。
吳天亮罵路波是有道理的,秘書告訴他,路波從雜木河水文站跑到流管處,不知跟鄧家英說了什麽,鄧家英就不管不顧地要去省城,起先說是找女兒,後來又說找秦繼舟。路波阻攔著,說吳書記還在辦公室等妳呢,怎麽著也得見過了書記再去。鄧家英破口大罵:“都這個時候了,我管他是書記還是地痞,滾他的流域治理吧,我要見我的小露。”遂關掉手機,命令司機往省城開。車子剛上路,鄧家英就倒在了車裏。路波見勢不妙,慌忙讓司機掉頭,直接將鄧家英送進市人民醫院。
吳天亮對“地痞”兩個字恨得咬牙切齒,鄧家英已不止壹次這麽罵他了。車子趕到市醫院,吳天亮問聞訊趕來迎接他的醫院院長:“怎麽回事,病情嚴重不?”院長肅穆著臉說:“暫時還不好說,估計是勞累過度引起的,我們正在緊急救治。”吳天亮沒說什麽,緊步往病房去。鄧家英還沒蘇醒過來,不過主治大夫說:“病人沒有生命危險,勞累加意外刺激,估計很快就會醒過來。”吳天亮奔到床前,確信鄧家英呼吸還在,只是臉色很差,轉身盯住路波:“是妳刺激了他?”路波臉色慘然,怔怔道:“哪有的事,就跟她談了點工作。”
“妳會跟他談工作?”吳天亮冷笑壹聲,跟主治大夫叮囑幾句,惡惡地沖路波說:“她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讓妳吃不了兜著走。”嚇得路波慌忙伸手再去試探鄧家英的呼吸。路波這輩子是讓吳天亮嚇下毛病了,當年修水庫,他是被管制被打倒的壹派,人家吳天亮當年是谷水的紅人,是水庫上革命勢力的代表,那時候吳天亮瞪壹眼,路波就要發抖,現在還這樣。
院長怕病房太鬧,更怕慢待了書記,小心翼翼地說:“病人需要安靜,還是請書記到辦公室做指示吧。”
吳天亮轉身離開病房,路波沒敢跟去,看著吳天亮他們的影子消失,長出壹口氣,心裏道:“能怪我嘛,換了妳家女兒被人拋棄,妳能不告訴妳老婆。”想著,眼裏竟噙了淚。這淚是為鄧家英噙的,自己再苦再難,是男人,男人是可以負任何重的,女人不能,女人不幸多了,那是很讓人揪心的。這麽想著,來到病床前,心裏默念道:“家英啊,妳好強了壹輩子,貌似啥也沒少掉,但妳這輩子,太虧了。現在小露又這樣,不公平,真不公平。”念著念著,心思又落到秦雨身上。路波本不打算將這些告訴鄧家英,小露走了後,他越想越氣,越想越不是滋味。秦雨跟小露,多般配的壹對,他吳家女兒憑啥插進壹腿來,難道就因她有個當書記的爸?再者,吳家女兒吳若涵是怎樣壹個人,路波再是清楚不過。那個名叫保羅的法國人跟他很友好,壹直拿他當老師呢,啥都跟他說了,而且有次就在雜木河,不,在雜木河西邊的紫水河,路波就親眼看見過吳若涵跟保羅在河裏那個。兩人脫得赤條條的,壹絲不掛,他們先是在河裏鬧,後來就到了河畔樹蔭下。法國人那樣咱管不著,可妳吳若涵是吳天亮的女兒呀,怎麽也能那樣不顧羞恥……路波壹激動,就跑到山下跟鄧家英說了,他是想讓鄧家英想想法子,最好找找秦繼舟,不能讓秦雨這麽好的孩子,被他吳家壹家人合著騙了。
哪料想……
路波現在有些後悔,早知如此,就該瞞著,不讓鄧家英知道。家英啊,妳可千萬不能倒下,妳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小露怎麽辦?
鄧家英偏在這時候醒了,睜開眼看了看路波,問,這是哪裏啊,我怎麽會在這裏躺著?路波趕忙起身,認真地看著她:“妳醒了啊,可把我嚇壞了,把吳書記也嚇壞了?”
“天亮,天亮在哪?”鄧家英掙紮著想起身,被路波阻止住了。路波說:“書記到院長辦公室去了,妳躺著別動。”
“告訴我,到底怎麽回事,不是去省城嗎,我怎麽會在醫院?”鄧家英真是記不起了,她腦子裏就急著小露。
“妳呀——”路波嘆壹聲,幫她把被子往上掖了掖,怕著涼,道:“做啥都玩命,還是年輕時候的性子,就不能柔點。流域都這樣了,妳還折騰個啥嘛。”路波去流管處見鄧家英,鄧家英正在埋頭整理治理方案,那方案提出好久了,市裏會議討論過多次,每次總有這樣或那樣的新想法提出,鄧家英就得壹遍遍地改,改來改去,功夫都下在了紙上,實際效果壹點也沒有。路波曾經嘲諷過,說吳天亮越來越像官僚,越來越會做官樣文章。現在不嘲諷了,感覺很沒意思。他是對這條河不抱指望了,抱不起。希望有多高,失望就有多重。壹個被河傷了壹輩子的人,再也傷不起傷不動了。
“不行,我不能這麽躺著,我得去省城,我要見老秦。”鄧家英忽然說。
“這哪成,妳都病這樣了,安心躺著。”正吵著,主治大夫進來了,壹看鄧家英醒了,臉上立馬有了喜色,簡單了解下病情,提議明天做全面檢查。鄧家英下意識地就說:“我不做檢查,我沒病,輸完這瓶液體我就走。”醫生笑笑,沒有反駁她,跟路波叮囑,有不良反應隨時找他。
第二天醫院果真要給鄧家英做全面檢查,鄧家英死活不同意,吵鬧著要出院,結果驚動了吳天亮。吳天亮派市委秘書長過來,協助做工作。鄧家英還是不同意,她沖路波發脾氣:“還磨蹭什麽,出院啊。”路波不敢不從,他在鄧家英面前向來如此。
主治醫生是個細心人,從鄧家英反常的表現中意識到什麽,聯系到發病原因還有鄧家英的氣色等,心裏有了疑惑。不過他沒把這些告訴別人,跟秘書長要了吳天亮辦公室電話,在電話裏很鄭重地要求對鄧家英進行全面檢查。吳天亮問有什麽不對嗎?醫生說這個我不能肯定,但她的身體絕對有問題,我請領導能重視。吳天亮不說話了,過了半小時,來到醫院。鄧家英已經跟路波離開了醫院。吳天亮又將主治醫生和院長叫來,當著院長面,主治醫生什麽也不說,只道是作為醫生,鄧家英沒在醫院做檢查,他心裏不放心。吳天亮察覺出什麽,讓主治醫跟他去辦公室。等到了市委,主治醫生才把心裏疑惑說出來。吳天亮臉登時白了,慘白。
“不會吧?”半天,他喃喃道。
“但願我的判斷有誤。”主治醫生說。吳天亮信得過這位醫生,去年他住院,就是這位主治醫看的,他沒再說話,但心裏已經在想辦法了。
鄧家英當天就趕到省城,女兒鄧朝露不在。雜木河回來的第二天,鄧朝露陪讀博期間的壹位女同學去了青海,同樣沒跟秦繼舟和所裏打招呼。秦繼舟正在發火呢,鄧家英進去了,秦繼舟脫口就說:“妳來得正好,妳這女兒是怎麽教育的,眼裏還有沒有組織,有沒有我這個老頭子?”鄧家英本來就委屈,從聽到女兒暗戀秦雨那壹刻,她的委屈就像河壹樣滾滾而來,這陣更像是火山,根本壓不住,壹看秦繼舟盛氣淩人的樣子,不假思索就道:“我女兒怎麽了,我女兒哪點讓您不順眼了,我把她交給您,讓您培養讓您教育,您又是怎麽教育的?”
“我……”秦繼舟還是第壹次遇到鄧家英沖他發火,壹時張口結舌,怔然地看著鄧家英。鄧家英壹不做二不休,連著又說了許多,全是委屈話傷心話,仿佛她今天來,就是沖秦繼舟倒苦水的。站在邊上的副所長章巖這時候才開口相勸:“大姐這是幹嘛呀,生這麽大氣不值,快請坐,我給大姐沏茶。”鄧家英也像是才發現房間裏還有壹個章巖,馬上收起臉上的不悅,換了笑臉道:“不好意思章所長,我今天……”
“沒事,沒事,誰也有不痛快的時候,大姐快坐,天熱,喝口茶消消火。”
秦繼舟卻說:“章巖妳去忙吧,我跟家英同誌有話說。”秦繼舟這是句牢騷話,剛才所以進門就沖鄧家英發火,還是章巖惹的禍。章巖不停地到他面前告鄧朝露狀,把他給惹惱了。
章巖臉上表情壹動,眼裏閃過壹縷嫉妒,說了句客氣話,走了。秦繼舟讓鄧家英坐,鄧家英楞是不坐,站在那裏較勁兒。秦繼舟呵呵壹笑:“怎麽,脾氣越來越大了嘛。”
“我哪敢,我這命只能受氣。”
“怎麽講?”
鄧家英忽然無語。她這麽急著趕來,完全是為了小露。小露深愛著秦雨,天啊,小露深愛著秦雨。這鬼丫頭,半個字不向她透露,害得她還四處為她張羅對象呢。怪不得呢,鄧家英既驚又喜,隨後,就徹底不安了。小露沒了愛情,她的愛情還沒來及表達,就丟了,丟了啊。鄧家英眼看要哭了,她原諒不了自己。
當媽的怎麽能疏忽到這程度!
現在,鄧家英想替女兒挽回,也想替自己抓住些什麽。她壹輩子不明不白,不能讓女兒也不明不白啊。可這些話她說不出,真的說不出。
她站在那裏,僵僵的,恨恨艾艾的目光不知往哪擱,最後竟撂下壹句莫名其妙的話:“妳秦家人就這麽欺負我們母女啊……”完了壹扭頭,沖出了那幢小樓。
秦繼舟這才察覺出什麽,等追出小樓,鄧家英已沒了影。副所長章巖緊跟著走出來,問:“怎麽走了,中午壹起吃飯啊。”秦繼舟怒瞪壹眼章巖,又往前追幾步,被幾個研究生擋住了。研究生拿著新寫的論文,想請教授指導。秦繼舟沒好氣地說:“哪兒涼快哪兒歇著去,我沒心思!”
看著秦繼舟發火的樣,章巖竊竊壹笑,拿出手機,給楚雅發了條短信,哼著歌回去了。
鄧家英沒地方可去,她登記了賓館,可壹分鐘也不想待在賓館,她來到黃河邊,望著滔滔東流的黃河水,望著泥沙俱下的這條河,腦子裏閃過壹幕幕畫面。這些畫面裏有她的愛情,有她的悲苦、淒涼,還有無盡的恨……
是的,恨。鄧家英現在最恨的,怕就是秦繼舟,壹個折磨她壹生的男人,壹個把她的心偷走卻再也不去光顧的男人。現在這個可惡的男人又利用他兒子,想讓她唯壹的女兒重陷萬劫不復的深淵。上天啊,妳怎麽能這麽殘忍。
不行,不能這麽認輸,絕不,我要為女兒奪回幸福。我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女兒被痛苦煎熬。女人失去心愛的男人,那是壹種怎樣的痛、怎樣的罪,鄧家英比誰都清楚。她果斷地掏出電話,給秦繼舟發了條短信,說要見他,就在黃河邊,黃河母親雕像那兒。過半天,秦繼舟回過來了短信,說自己正忙,有個報告今天必須交出去,晚上吧,晚上他們見面。
晚上就晚上,以為我怕妳啊。鄧家英被某種力量鼓舞著,鞭策著,似乎已經顧不得自己了,心中就壹個想法,要為女兒爭取,她已經輸得壹無所有了,要是女兒再輸個幹凈,這輩子,她還活個啥?
黃河邊的這座城市,像個大褲衩,從東邊大青山那兒甩出來,兩條腿壹條走南,走出細長的幾條街,壹條往北甩,甩出壹大片坑坑窪窪的風景。黃河慢條斯理從中間穿過,將這座城市弄得陰不陰陽不陽。說是北方城市吧,它有山有水,氣候也不是太暴烈,性情也還算溫柔。說是南方城市吧,又沒有壹點委婉樣,粗粗糙糙,讓人站哪兒也不覺舒服。鄧家英百無聊賴地在黃河邊坐了壹個下午,日頭照她身上,照出壹身接壹身的虛汗來。那是身體越來越虛的表現,她知道,體內的病毒正在以不可阻擋的速度漫延,那種可怕的細胞正像憤青壹樣猖獗著,惡毒地想把她放倒在某個早晨或正午,所以她必須時刻警惕,在追回女兒的愛情與幸福之前,絕不能倒下。她抱著電話,琢磨著要不要給秦雨那小子發條短信或直接打過去電話。臭小子,別的本事沒學下,妳爸那套倒是學個滴水不漏。我就不信妳小子沒察覺,還怪模怪樣裝出無辜的樣子,好像我家小露不配妳似的。她吳家女兒算什麽,算什麽嘛。
鄧家英越想越氣,握著電話的手不停地發抖。
但真要往外撥那個號時,她又猶豫了。秦雨這小子,眼睛裏有毒啊,加上她母親的教唆,還不知怎麽恨她呢,能聽她的?鄧家英就這麽恨著,惱著,狂躁著,終於等到了下午。秦繼舟打來電話,說在壹家酒店訂了座,要跟她壹起吃飯。
飯吃得尷尬無味,菜倒是點了不少,可鄧家英哪有胃口?秦繼舟倒是老到,不急不躁,中間還談起了工作,說現在學術界風氣越來越不正,這麽下去,學術兩個字就被玷汙了。鄧家英沒好氣地說:“這些年玷汙掉的東西還少,憑什麽學術界要獨留幹凈?”
“妳這思想要不得,怎麽著妳也是知識分子,學術界幹凈不幹凈,跟妳還是有關系嘛。”秦繼舟壹本正經道。
“跟我有啥關系,我是女人,我只知道女人不能老是受人欺負。”鄧家英語氣很沖。
“妳看妳,又來了。家英啊,妳這輩子……”秦繼舟做深思狀,不往下說了。往下說鄧家英也不愛聽,惡聲惡氣打斷他:“我這輩子咋了,我這輩子還不就……”她差點就把堵在心裏那話說出來。秦繼舟怕了,擺擺手道:“咱們不吵,不吵好不,吃菜,有啥事吃飽肚子再說。”
“我吃不下!”鄧家英“啪”地將筷子摔桌上,兩只手環抱著坐在了那。秦繼舟搖頭道:“妳這性子就不能改壹改,這是酒店,要註意影響嘛,看看四周,誰像妳這樣?”
“我註意不了。”鄧家英嘴上沖著,眼睛卻四下瞅起來,見有人怪怪地瞪著她,看稀有動物似的,知趣地往前俯了俯了身子,拿起筷子夾菜了,默無聲息的,就將夾起的第壹塊魚給了秦繼舟。秦繼舟也沒客氣,心安理得吃起來。鄧家英默默看著他吃,他的吃相還是那麽斯文,仿佛超然於世外,吐魚刺的動作都那麽優雅。這個人啊,鄧家英神思壹下又恍惚,這個男人到底是魔還是鬼,為什麽總給她壹種擺脫不了的感覺?
鄧家英的思緒差點又要飛到很多年前了,那時候……
酒店不能談事,秦繼舟說回去談。鄧家英不想去北方大學那幢小樓,但秦繼舟又從來不跟她在賓館見面,多年來都這樣,只好跟著他來到研究所。秦繼舟並不住在辦公室,二樓西側有間空房,他把自己臨時安置在那裏。壹進門,鄧家英就嗅到壹股黴氣,等看清屋子裏的亂象,心裏更是酸楚。唉,這叫什麽日子呢,從不愛惜自己。鄧家英也不管自己正生秦繼舟的氣,包壹丟,急著整理起屋子衛生來,壹邊收拾壹邊嘮叨:“看看妳,看看妳啊,老了卻不知珍惜自己了,放著那麽好的家不安穩待著,跑單位受這份罪。”秦繼舟也不阻攔鄧家英,反倒很有理地說:“我為什麽要回家,為什麽要跟壹個愚蠢的人守在壹起?”
“是她愚蠢還是妳愚蠢,看看妳啊,臭襪子壹堆,還有這衣服,都發臭了,好歹妳也是專家,是國寶,就這麽糟蹋自己?”說著,抱起壹堆臟衣服,拿了臉盆去衛生間。聽見嘩嘩的水響,秦繼舟壹點不覺有什麽不自在,仿佛鄧家英做這些天經地義。其實不,秦繼舟壓根意識不到哪些事該老婆做,哪些事該別人做。在他看來,能做的事誰做也無所謂,不能做的事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做。鄧家英替他洗衣服的時候,他居然壹屁股坐下來,攤開壹份材料,他覺得鄧家英今天來得正好,關於流域下壹步治理他有幾個新想法,要跟鄧家英好好談談。
不出壹小時,衣服洗了,屋子打掃整潔了,床和沙發什麽的也都整理幹凈。鄧家英折騰出壹身汗,擦汗的時候,猛感覺乳房那兒壹陣劇痛,眉頭痛苦地壹皺,強行用手捂住,又怕秦繼舟看見,硬撐著站直了身子。秦繼舟哪裏有心情管她,不停地在紙上忙著寫什麽,寫壹會問過話來:“去年降雨量比前年平均數字降了多少?”
鄧家英話都到嘴邊了,突然又說:“不知道!”
“妳怎麽能不知道,這個數字妳要裝腦子裏,我辦公室有,要不妳跑壹趟,還有上期的冰川雜誌妳也拿來,上面有篇文章,妳要看。”
“不去,我累了。”鄧家英賭氣似的說道。
“那妳先休息壹會,這篇文章我想呈給發改委,應該讓他們有個清醒的認識了,再不能遮遮掩掩。對了,省裏最近出臺的政策妳怎麽看,我感覺現在是措施越來越多,力度越來越大,效果越來越差,惡性循環啊。”他壹邊埋頭驗算數字,壹邊跟鄧家英說自己的看法,半天聽不到鄧家英回應,回頭壹看,鄧家英竟栽倒在床上。
“家英,妳怎麽了?”秦繼舟扔掉筆,撲向床邊。鄧家英臉色發白,嘴唇發紫,人是昏厥過去的。秦繼舟嚇壞了,好在他不缺經驗,當年修水庫,他見過許多累倒餓倒的人,也見識過農民們急救人的法子,壹邊大聲喚鄧家英的名字,壹邊掐住人中。半天,鄧家英蘇醒過來,臉色蒼白地說:“我想女兒,我家小露可憐啊。”
“家英妳別亂想。”
恰在這時,虛掩著的門砰地被推開,楚雅壹頭撞進來,秦繼舟雙手正抱著鄧家英,臉幾乎要貼到鄧家英臉上。楚雅的怒聲壹下就有了。
“天啊,妳們,妳們……”
上遊堅決不放水,弄得上下遊關系越來越緊張,市裏眾說紛紜,圍繞著這條河,圍繞著流域,大家各執壹詞,意見壹時很難統壹。吳天亮又不敢強行責令上遊谷川開閘放水,怕將矛盾進壹步激化。
但是水的問題不解決,他這個市委書記就別想當安穩。
下班時間早已過了,吳天亮還在辦公室煎熬著,他在等流域管理處處長鄧家英。吳天亮早年在管理處做過處長,後來到市裏擔任領導,兩年前他就任市委書記,將鄧家英硬性安排在這個職位上,目的就是期望鄧家英勵精圖治,能把流域這盤死棋下成活棋。可事實表明,到現在為止,流域這盤棋還是下不活,非但下不活,而且眼看著下不下去了。
時間壹分壹秒過去,大樓裏壹片安靜,說好七點二十在他辦公室見,現在兩個小時過去了,還不見鄧家英人影。困在辦公室的吳天亮心裏很不是滋味。要說市委書記讓壹個下屬來見他,簡直就是不張嘴都能做到的事,哪還用得著焦灼地去等。可鄧家英這個下屬實在不同,她不但讓吳天亮等,還讓吳天亮等得心裏生煙,等得想發火又發不出來。那天吳天亮在會上動議,試圖用高壓政策,強行從上遊谷川調水,以解下遊沙湖燃眉之急,遭到了鄧家英等人的強烈反對。鄧家英竟然當著那麽多人面,說他不顧自然規律,為了政績,壹次次人為地加劇河的悲劇。氣得吳天亮差點摔了杯子。鄧家英竟不依不饒,又跟他算起了移民賬,算起了下遊打井開荒的賬。移民和打井開荒都是吳天亮上任後谷水市推出的新政,鄧家英這樣做,等於是在攻擊他。吳天亮忍無可忍,厲聲批評了鄧家英壹通,沒想到鄧家英當場提出辭職,說不幹了,退休回家!
娘的,都是沖我撒脾氣!吳天亮罵壹聲,擡起手腕看表,九點過壹刻。他跟自己說,再等十分鐘,要是還不來,就同意她的辭職要求,想幹嘛幹嘛去!這樣下去絕不是法子,都跟他撂挑子,關鍵時刻壹個也指靠不住,這書記還怎麽當,流域還怎麽治理?
十分鐘很快過去了,樓裏照樣沒有動靜。吳天亮脾氣越發大,抓起電話打給秘書:“我讓妳催她怎麽催得到現在還不見影?”秘書嘟囔了幾聲,從對面那扇門裏走過來,小心翼翼地說:“壹小時前鄧處長電話還通著,現在怎麽也打不通。”
“打不通派車去找啊,難道讓我親自去找她?”吳天亮惱了。豈料十分鐘後,秘書慌慌張張跑進來說:“不好了,鄧處長昏倒在路上,目前正在醫院搶救。”
“什麽?”吳天亮大驚失色,等問明情況,馬上驅車往醫院趕。路上他將電話打給路波,質問怎麽回事?路波吞吞吐吐,不肯說實話。吳天亮更是壓不住火,罵路波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廢物壹個。
吳天亮罵路波是有道理的,秘書告訴他,路波從雜木河水文站跑到流管處,不知跟鄧家英說了什麽,鄧家英就不管不顧地要去省城,起先說是找女兒,後來又說找秦繼舟。路波阻攔著,說吳書記還在辦公室等妳呢,怎麽著也得見過了書記再去。鄧家英破口大罵:“都這個時候了,我管他是書記還是地痞,滾他的流域治理吧,我要見我的小露。”遂關掉手機,命令司機往省城開。車子剛上路,鄧家英就倒在了車裏。路波見勢不妙,慌忙讓司機掉頭,直接將鄧家英送進市人民醫院。
吳天亮對“地痞”兩個字恨得咬牙切齒,鄧家英已不止壹次這麽罵他了。車子趕到市醫院,吳天亮問聞訊趕來迎接他的醫院院長:“怎麽回事,病情嚴重不?”院長肅穆著臉說:“暫時還不好說,估計是勞累過度引起的,我們正在緊急救治。”吳天亮沒說什麽,緊步往病房去。鄧家英還沒蘇醒過來,不過主治大夫說:“病人沒有生命危險,勞累加意外刺激,估計很快就會醒過來。”吳天亮奔到床前,確信鄧家英呼吸還在,只是臉色很差,轉身盯住路波:“是妳刺激了他?”路波臉色慘然,怔怔道:“哪有的事,就跟她談了點工作。”
“妳會跟他談工作?”吳天亮冷笑壹聲,跟主治大夫叮囑幾句,惡惡地沖路波說:“她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讓妳吃不了兜著走。”嚇得路波慌忙伸手再去試探鄧家英的呼吸。路波這輩子是讓吳天亮嚇下毛病了,當年修水庫,他是被管制被打倒的壹派,人家吳天亮當年是谷水的紅人,是水庫上革命勢力的代表,那時候吳天亮瞪壹眼,路波就要發抖,現在還這樣。
院長怕病房太鬧,更怕慢待了書記,小心翼翼地說:“病人需要安靜,還是請書記到辦公室做指示吧。”
吳天亮轉身離開病房,路波沒敢跟去,看著吳天亮他們的影子消失,長出壹口氣,心裏道:“能怪我嘛,換了妳家女兒被人拋棄,妳能不告訴妳老婆。”想著,眼裏竟噙了淚。這淚是為鄧家英噙的,自己再苦再難,是男人,男人是可以負任何重的,女人不能,女人不幸多了,那是很讓人揪心的。這麽想著,來到病床前,心裏默念道:“家英啊,妳好強了壹輩子,貌似啥也沒少掉,但妳這輩子,太虧了。現在小露又這樣,不公平,真不公平。”念著念著,心思又落到秦雨身上。路波本不打算將這些告訴鄧家英,小露走了後,他越想越氣,越想越不是滋味。秦雨跟小露,多般配的壹對,他吳家女兒憑啥插進壹腿來,難道就因她有個當書記的爸?再者,吳家女兒吳若涵是怎樣壹個人,路波再是清楚不過。那個名叫保羅的法國人跟他很友好,壹直拿他當老師呢,啥都跟他說了,而且有次就在雜木河,不,在雜木河西邊的紫水河,路波就親眼看見過吳若涵跟保羅在河裏那個。兩人脫得赤條條的,壹絲不掛,他們先是在河裏鬧,後來就到了河畔樹蔭下。法國人那樣咱管不著,可妳吳若涵是吳天亮的女兒呀,怎麽也能那樣不顧羞恥……路波壹激動,就跑到山下跟鄧家英說了,他是想讓鄧家英想想法子,最好找找秦繼舟,不能讓秦雨這麽好的孩子,被他吳家壹家人合著騙了。
哪料想……
路波現在有些後悔,早知如此,就該瞞著,不讓鄧家英知道。家英啊,妳可千萬不能倒下,妳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小露怎麽辦?
鄧家英偏在這時候醒了,睜開眼看了看路波,問,這是哪裏啊,我怎麽會在這裏躺著?路波趕忙起身,認真地看著她:“妳醒了啊,可把我嚇壞了,把吳書記也嚇壞了?”
“天亮,天亮在哪?”鄧家英掙紮著想起身,被路波阻止住了。路波說:“書記到院長辦公室去了,妳躺著別動。”
“告訴我,到底怎麽回事,不是去省城嗎,我怎麽會在醫院?”鄧家英真是記不起了,她腦子裏就急著小露。
“妳呀——”路波嘆壹聲,幫她把被子往上掖了掖,怕著涼,道:“做啥都玩命,還是年輕時候的性子,就不能柔點。流域都這樣了,妳還折騰個啥嘛。”路波去流管處見鄧家英,鄧家英正在埋頭整理治理方案,那方案提出好久了,市裏會議討論過多次,每次總有這樣或那樣的新想法提出,鄧家英就得壹遍遍地改,改來改去,功夫都下在了紙上,實際效果壹點也沒有。路波曾經嘲諷過,說吳天亮越來越像官僚,越來越會做官樣文章。現在不嘲諷了,感覺很沒意思。他是對這條河不抱指望了,抱不起。希望有多高,失望就有多重。壹個被河傷了壹輩子的人,再也傷不起傷不動了。
“不行,我不能這麽躺著,我得去省城,我要見老秦。”鄧家英忽然說。
“這哪成,妳都病這樣了,安心躺著。”正吵著,主治大夫進來了,壹看鄧家英醒了,臉上立馬有了喜色,簡單了解下病情,提議明天做全面檢查。鄧家英下意識地就說:“我不做檢查,我沒病,輸完這瓶液體我就走。”醫生笑笑,沒有反駁她,跟路波叮囑,有不良反應隨時找他。
第二天醫院果真要給鄧家英做全面檢查,鄧家英死活不同意,吵鬧著要出院,結果驚動了吳天亮。吳天亮派市委秘書長過來,協助做工作。鄧家英還是不同意,她沖路波發脾氣:“還磨蹭什麽,出院啊。”路波不敢不從,他在鄧家英面前向來如此。
主治醫生是個細心人,從鄧家英反常的表現中意識到什麽,聯系到發病原因還有鄧家英的氣色等,心裏有了疑惑。不過他沒把這些告訴別人,跟秘書長要了吳天亮辦公室電話,在電話裏很鄭重地要求對鄧家英進行全面檢查。吳天亮問有什麽不對嗎?醫生說這個我不能肯定,但她的身體絕對有問題,我請領導能重視。吳天亮不說話了,過了半小時,來到醫院。鄧家英已經跟路波離開了醫院。吳天亮又將主治醫生和院長叫來,當著院長面,主治醫生什麽也不說,只道是作為醫生,鄧家英沒在醫院做檢查,他心裏不放心。吳天亮察覺出什麽,讓主治醫跟他去辦公室。等到了市委,主治醫生才把心裏疑惑說出來。吳天亮臉登時白了,慘白。
“不會吧?”半天,他喃喃道。
“但願我的判斷有誤。”主治醫生說。吳天亮信得過這位醫生,去年他住院,就是這位主治醫看的,他沒再說話,但心裏已經在想辦法了。
鄧家英當天就趕到省城,女兒鄧朝露不在。雜木河回來的第二天,鄧朝露陪讀博期間的壹位女同學去了青海,同樣沒跟秦繼舟和所裏打招呼。秦繼舟正在發火呢,鄧家英進去了,秦繼舟脫口就說:“妳來得正好,妳這女兒是怎麽教育的,眼裏還有沒有組織,有沒有我這個老頭子?”鄧家英本來就委屈,從聽到女兒暗戀秦雨那壹刻,她的委屈就像河壹樣滾滾而來,這陣更像是火山,根本壓不住,壹看秦繼舟盛氣淩人的樣子,不假思索就道:“我女兒怎麽了,我女兒哪點讓您不順眼了,我把她交給您,讓您培養讓您教育,您又是怎麽教育的?”
“我……”秦繼舟還是第壹次遇到鄧家英沖他發火,壹時張口結舌,怔然地看著鄧家英。鄧家英壹不做二不休,連著又說了許多,全是委屈話傷心話,仿佛她今天來,就是沖秦繼舟倒苦水的。站在邊上的副所長章巖這時候才開口相勸:“大姐這是幹嘛呀,生這麽大氣不值,快請坐,我給大姐沏茶。”鄧家英也像是才發現房間裏還有壹個章巖,馬上收起臉上的不悅,換了笑臉道:“不好意思章所長,我今天……”
“沒事,沒事,誰也有不痛快的時候,大姐快坐,天熱,喝口茶消消火。”
秦繼舟卻說:“章巖妳去忙吧,我跟家英同誌有話說。”秦繼舟這是句牢騷話,剛才所以進門就沖鄧家英發火,還是章巖惹的禍。章巖不停地到他面前告鄧朝露狀,把他給惹惱了。
章巖臉上表情壹動,眼裏閃過壹縷嫉妒,說了句客氣話,走了。秦繼舟讓鄧家英坐,鄧家英楞是不坐,站在那裏較勁兒。秦繼舟呵呵壹笑:“怎麽,脾氣越來越大了嘛。”
“我哪敢,我這命只能受氣。”
“怎麽講?”
鄧家英忽然無語。她這麽急著趕來,完全是為了小露。小露深愛著秦雨,天啊,小露深愛著秦雨。這鬼丫頭,半個字不向她透露,害得她還四處為她張羅對象呢。怪不得呢,鄧家英既驚又喜,隨後,就徹底不安了。小露沒了愛情,她的愛情還沒來及表達,就丟了,丟了啊。鄧家英眼看要哭了,她原諒不了自己。
當媽的怎麽能疏忽到這程度!
現在,鄧家英想替女兒挽回,也想替自己抓住些什麽。她壹輩子不明不白,不能讓女兒也不明不白啊。可這些話她說不出,真的說不出。
她站在那裏,僵僵的,恨恨艾艾的目光不知往哪擱,最後竟撂下壹句莫名其妙的話:“妳秦家人就這麽欺負我們母女啊……”完了壹扭頭,沖出了那幢小樓。
秦繼舟這才察覺出什麽,等追出小樓,鄧家英已沒了影。副所長章巖緊跟著走出來,問:“怎麽走了,中午壹起吃飯啊。”秦繼舟怒瞪壹眼章巖,又往前追幾步,被幾個研究生擋住了。研究生拿著新寫的論文,想請教授指導。秦繼舟沒好氣地說:“哪兒涼快哪兒歇著去,我沒心思!”
看著秦繼舟發火的樣,章巖竊竊壹笑,拿出手機,給楚雅發了條短信,哼著歌回去了。
鄧家英沒地方可去,她登記了賓館,可壹分鐘也不想待在賓館,她來到黃河邊,望著滔滔東流的黃河水,望著泥沙俱下的這條河,腦子裏閃過壹幕幕畫面。這些畫面裏有她的愛情,有她的悲苦、淒涼,還有無盡的恨……
是的,恨。鄧家英現在最恨的,怕就是秦繼舟,壹個折磨她壹生的男人,壹個把她的心偷走卻再也不去光顧的男人。現在這個可惡的男人又利用他兒子,想讓她唯壹的女兒重陷萬劫不復的深淵。上天啊,妳怎麽能這麽殘忍。
不行,不能這麽認輸,絕不,我要為女兒奪回幸福。我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女兒被痛苦煎熬。女人失去心愛的男人,那是壹種怎樣的痛、怎樣的罪,鄧家英比誰都清楚。她果斷地掏出電話,給秦繼舟發了條短信,說要見他,就在黃河邊,黃河母親雕像那兒。過半天,秦繼舟回過來了短信,說自己正忙,有個報告今天必須交出去,晚上吧,晚上他們見面。
晚上就晚上,以為我怕妳啊。鄧家英被某種力量鼓舞著,鞭策著,似乎已經顧不得自己了,心中就壹個想法,要為女兒爭取,她已經輸得壹無所有了,要是女兒再輸個幹凈,這輩子,她還活個啥?
黃河邊的這座城市,像個大褲衩,從東邊大青山那兒甩出來,兩條腿壹條走南,走出細長的幾條街,壹條往北甩,甩出壹大片坑坑窪窪的風景。黃河慢條斯理從中間穿過,將這座城市弄得陰不陰陽不陽。說是北方城市吧,它有山有水,氣候也不是太暴烈,性情也還算溫柔。說是南方城市吧,又沒有壹點委婉樣,粗粗糙糙,讓人站哪兒也不覺舒服。鄧家英百無聊賴地在黃河邊坐了壹個下午,日頭照她身上,照出壹身接壹身的虛汗來。那是身體越來越虛的表現,她知道,體內的病毒正在以不可阻擋的速度漫延,那種可怕的細胞正像憤青壹樣猖獗著,惡毒地想把她放倒在某個早晨或正午,所以她必須時刻警惕,在追回女兒的愛情與幸福之前,絕不能倒下。她抱著電話,琢磨著要不要給秦雨那小子發條短信或直接打過去電話。臭小子,別的本事沒學下,妳爸那套倒是學個滴水不漏。我就不信妳小子沒察覺,還怪模怪樣裝出無辜的樣子,好像我家小露不配妳似的。她吳家女兒算什麽,算什麽嘛。
鄧家英越想越氣,握著電話的手不停地發抖。
但真要往外撥那個號時,她又猶豫了。秦雨這小子,眼睛裏有毒啊,加上她母親的教唆,還不知怎麽恨她呢,能聽她的?鄧家英就這麽恨著,惱著,狂躁著,終於等到了下午。秦繼舟打來電話,說在壹家酒店訂了座,要跟她壹起吃飯。
飯吃得尷尬無味,菜倒是點了不少,可鄧家英哪有胃口?秦繼舟倒是老到,不急不躁,中間還談起了工作,說現在學術界風氣越來越不正,這麽下去,學術兩個字就被玷汙了。鄧家英沒好氣地說:“這些年玷汙掉的東西還少,憑什麽學術界要獨留幹凈?”
“妳這思想要不得,怎麽著妳也是知識分子,學術界幹凈不幹凈,跟妳還是有關系嘛。”秦繼舟壹本正經道。
“跟我有啥關系,我是女人,我只知道女人不能老是受人欺負。”鄧家英語氣很沖。
“妳看妳,又來了。家英啊,妳這輩子……”秦繼舟做深思狀,不往下說了。往下說鄧家英也不愛聽,惡聲惡氣打斷他:“我這輩子咋了,我這輩子還不就……”她差點就把堵在心裏那話說出來。秦繼舟怕了,擺擺手道:“咱們不吵,不吵好不,吃菜,有啥事吃飽肚子再說。”
“我吃不下!”鄧家英“啪”地將筷子摔桌上,兩只手環抱著坐在了那。秦繼舟搖頭道:“妳這性子就不能改壹改,這是酒店,要註意影響嘛,看看四周,誰像妳這樣?”
“我註意不了。”鄧家英嘴上沖著,眼睛卻四下瞅起來,見有人怪怪地瞪著她,看稀有動物似的,知趣地往前俯了俯了身子,拿起筷子夾菜了,默無聲息的,就將夾起的第壹塊魚給了秦繼舟。秦繼舟也沒客氣,心安理得吃起來。鄧家英默默看著他吃,他的吃相還是那麽斯文,仿佛超然於世外,吐魚刺的動作都那麽優雅。這個人啊,鄧家英神思壹下又恍惚,這個男人到底是魔還是鬼,為什麽總給她壹種擺脫不了的感覺?
鄧家英的思緒差點又要飛到很多年前了,那時候……
酒店不能談事,秦繼舟說回去談。鄧家英不想去北方大學那幢小樓,但秦繼舟又從來不跟她在賓館見面,多年來都這樣,只好跟著他來到研究所。秦繼舟並不住在辦公室,二樓西側有間空房,他把自己臨時安置在那裏。壹進門,鄧家英就嗅到壹股黴氣,等看清屋子裏的亂象,心裏更是酸楚。唉,這叫什麽日子呢,從不愛惜自己。鄧家英也不管自己正生秦繼舟的氣,包壹丟,急著整理起屋子衛生來,壹邊收拾壹邊嘮叨:“看看妳,看看妳啊,老了卻不知珍惜自己了,放著那麽好的家不安穩待著,跑單位受這份罪。”秦繼舟也不阻攔鄧家英,反倒很有理地說:“我為什麽要回家,為什麽要跟壹個愚蠢的人守在壹起?”
“是她愚蠢還是妳愚蠢,看看妳啊,臭襪子壹堆,還有這衣服,都發臭了,好歹妳也是專家,是國寶,就這麽糟蹋自己?”說著,抱起壹堆臟衣服,拿了臉盆去衛生間。聽見嘩嘩的水響,秦繼舟壹點不覺有什麽不自在,仿佛鄧家英做這些天經地義。其實不,秦繼舟壓根意識不到哪些事該老婆做,哪些事該別人做。在他看來,能做的事誰做也無所謂,不能做的事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做。鄧家英替他洗衣服的時候,他居然壹屁股坐下來,攤開壹份材料,他覺得鄧家英今天來得正好,關於流域下壹步治理他有幾個新想法,要跟鄧家英好好談談。
不出壹小時,衣服洗了,屋子打掃整潔了,床和沙發什麽的也都整理幹凈。鄧家英折騰出壹身汗,擦汗的時候,猛感覺乳房那兒壹陣劇痛,眉頭痛苦地壹皺,強行用手捂住,又怕秦繼舟看見,硬撐著站直了身子。秦繼舟哪裏有心情管她,不停地在紙上忙著寫什麽,寫壹會問過話來:“去年降雨量比前年平均數字降了多少?”
鄧家英話都到嘴邊了,突然又說:“不知道!”
“妳怎麽能不知道,這個數字妳要裝腦子裏,我辦公室有,要不妳跑壹趟,還有上期的冰川雜誌妳也拿來,上面有篇文章,妳要看。”
“不去,我累了。”鄧家英賭氣似的說道。
“那妳先休息壹會,這篇文章我想呈給發改委,應該讓他們有個清醒的認識了,再不能遮遮掩掩。對了,省裏最近出臺的政策妳怎麽看,我感覺現在是措施越來越多,力度越來越大,效果越來越差,惡性循環啊。”他壹邊埋頭驗算數字,壹邊跟鄧家英說自己的看法,半天聽不到鄧家英回應,回頭壹看,鄧家英竟栽倒在床上。
“家英,妳怎麽了?”秦繼舟扔掉筆,撲向床邊。鄧家英臉色發白,嘴唇發紫,人是昏厥過去的。秦繼舟嚇壞了,好在他不缺經驗,當年修水庫,他見過許多累倒餓倒的人,也見識過農民們急救人的法子,壹邊大聲喚鄧家英的名字,壹邊掐住人中。半天,鄧家英蘇醒過來,臉色蒼白地說:“我想女兒,我家小露可憐啊。”
“家英妳別亂想。”
恰在這時,虛掩著的門砰地被推開,楚雅壹頭撞進來,秦繼舟雙手正抱著鄧家英,臉幾乎要貼到鄧家英臉上。楚雅的怒聲壹下就有了。
“天啊,妳們,妳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