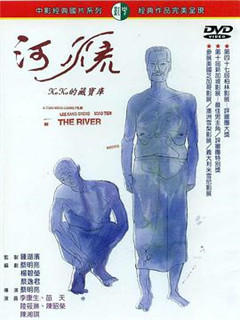- [ 免費 ] 第1章 河與沙漠
- [ 免費 ] 第2章 母親的不適
- [ 免費 ] 第3章 新的壹天
- [ 免費 ] 第4章 調查
- [ 免費 ] 第5章 壞消息
- [ 免費 ] 第6章 草原上
- [ 免費 ] 第7章 水文站
- [ 免費 ] 第8章 陸伯伯
- [ 免費 ] 第9章 水
- [ 免費 ] 第10章 新聞人物
- [ 免費 ] 第11章
- [ 免費 ] 第12章
- [ 免費 ] 第13章
- [ 免費 ] 第14章
- [ 免費 ] 第15章
- [ 免費 ] 第16章
- [ 免費 ] 第17章
- [ 免費 ] 第18章
- [ 免費 ] 第19章
- [ 免費 ] 第20章
- [ 免費 ] 第21章
- [ 免費 ] 第22章
- [ 免費 ] 第23章
- [ 免費 ] 第24章
- [ 免費 ] 第25章
- [ 免費 ] 第26章
- [ 免費 ] 第27章
- [ 免費 ] 第28章
- [ 免費 ] 第29章
- [ 免費 ] 第30章
- [ 免費 ] 第31章
- [ 免費 ] 第32章
- [ 免費 ] 第33章
- [ 免費 ] 第34章
- [ 免費 ] 第35章
- [ 免費 ] 第36章
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AA+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
简
第15章
2018-9-27 20:33
那壹年的很多事至今還刻在秦繼舟腦子裏,不,深深地烙心上。只是,輕易不敢翻出來。壹翻出來,秦繼舟會看到別樣的東西。所以他怕,所以他深深地藏著。
他是壹個躲在記憶暗處的人。
每次踏上祁連,秦繼舟總要生出不少懺悔,這懺悔有時來得毫沒來由,卻又極其強烈,仿佛,流域變成這樣,是他壹手造成的。這是壹種非常可怕的感觸,但又抵擋不了,仿佛壹口深井,已把他牢牢困住。天旱得厲害,前些日子雖然降過壹場雨,但在秦繼舟眼裏,那不能叫雨,頂多是老天掉下幾個淚渣子。有雨的日子壹去不復返,很多日子都壹去不復返。人生就是這樣,老在懺悔中往前走,懺悔成了活著的理由。
這次出來,好像是生了老婆和兒子的氣,其實不,怎麽可能呢,如果生他們的氣,秦繼舟相信自己是活不到現在的。尤其老婆楚雅,他似乎已經習慣,愛鬧鬧去吧,他已沒有壹點反抗的欲望。
人是不能見啥也反抗的,反抗有時候是那麽的無濟於事。秦繼舟是動過離婚念頭的。他們的結合在當年來說是件挺轟動的事,水庫修壹半時,北方大學突然組織了學習團,到龍鳳峽等幾個水庫接受教育。楚雅興奮地來到龍鳳峽工地,見面就說:“我爸誇妳呢,幹得好棒。”
她爸那時是北方大學副書記,她媽更是不簡單,在省裏。秦繼舟在下面的壹應表現,都通過特殊渠道傳到他們夫婦耳朵裏,讓女兒到龍鳳峽工地,不能不說有某種目的。
這目的很快被挑到明處。秦繼舟因為成功攻破龍首山爆破難關,將全新的爆破辦法手把手教給工地爆破人員,壹時成了英雄,好多記者來到龍鳳峽,大力報道他的英雄事跡。很快,壹道嘉獎令頒了下來,給他親手戴上光榮花的,就是自己未來的嶽母,壹個漂亮得讓人咋舌的中年女人。此後不久,壹個落雨的夜晚,秦繼舟被請進谷水地委招待所,跟他談話的是楚雅的父母。他們說:“我們已決定把女兒嫁給妳了,有妳這樣壹個紅色樣板做我們的女婿,我們很高興。妳有什麽想法,可以說出來。”說完後,夫妻倆對望壹眼,等待他的回答。秦繼舟好不吃驚,那時候他腦子裏真是沒有結婚概念的,就連戀愛這樣的想法也不敢有,覺得是種恥辱。所有的人都在為社會主義建設奮鬥,都在鼓足幹勁,大幹快上,他怎麽能談情說愛呢?資產階級的東西萬萬要不得啊。可跟他談話的是組織,是……他垂下頭,半天不作聲。楚雅母親矜矜壹笑:“看來小秦是同意了,好吧,我們做父母的就不多說什麽了,妳們還有壹段時間,可以互相接觸壹下,增加革命感情嘛,時機成熟時,我們會通知妳,婚禮我們會抓緊張羅的。”
說完,夫婦倆就走了。秦繼舟還沒回過神來,就有兩撥人先後走進來,都是代表組織跟他談話,要他珍惜這機會,要他接受組織考驗,要他拿出滿腔熱情來,迎接挑戰。他們把愛情也說成是挑戰,口氣就跟要他赴湯蹈火壹樣。秦繼舟還能說什麽呢,那是壹個組織決定壹切的年代,個人在組織面前,除了響應和服從,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
有發言權的是楚雅。她突然做出壹個決定,留在龍鳳峽水庫不走了,要跟秦繼舟並肩戰鬥。戰鬥的結果就是在龍鳳峽水庫大壩將要合龍的前壹天,在水庫工地舉行了神聖的婚禮。
而在那壹天,水庫工地上同時發生壹件離奇事,鐵姑娘隊副隊長鄧家英失蹤了,派出去很多人都沒找到,她的父親鄧源森怒氣沖沖說:“姓秦的,妳真他媽不是東西,我女兒要有個三長兩短,我把妳丟河裏當沙洗!”
那壹刻,秦繼舟才恍然明白,這對父女這麽長時間裏對他隱藏了什麽。天啊,怎麽可能,怎麽可能嘛!他大張著嘴,吃驚地望著鄧源森。然後回過目光,盯住自己的準妻子。他的目光瞬間變得迷茫,變得恐懼而不安,不知所措。楚雅及時地說:“繼舟妳鎮定點,不就丟了壹個村姑,妳驚慌什麽?”又罵鄧源森:“這個男人好粗野,他有什麽權利教訓妳?這裏的人咋都這麽粗野啊——”
粗野的並不是別人,正是楚雅。這是婚後很久秦繼舟才明白過來的,可是晚矣。那時候他們已經有了兒子秦雨,在兒子秦雨之前,楚雅不小心還流過壹次產。當時龍鳳峽水庫大壩已經合龍,秦繼舟又熱情不減地去了南營水庫,懷孕的楚雅跟在他後面,誰勸也不回去。他們像壹對發了瘋的羊,認為只有修水庫的地方才有草。其實秦繼舟心裏明白,楚雅是怕他。那個時候楚雅已經知道鄧家英對他是怎麽回事了,工地上的人都在風言風語,說他們的鄧家英太傻了,人家秦大學怎麽會看上她呢?人家是省城來的,又是大學老師,後面還站著有權有勢的嶽父母,怎麽可能對壹個鄉下妹子動情呢?很快有人反駁,鄉下妹子咋了,鄉下妹子就不能喜歡別人?馬上又有人嘆:“能,咋不能呢,可喜歡了又能咋,差點把命搭上,喜歡不起啊。”
是差點把命搭上。
得知秦繼舟要跟楚雅結婚,要成為省裏來的楚雅的丈夫,鄧家英哭了幾夜,然後上了香林寺,她要到香林寺當尼姑。沒想到寺裏不久,害了壹場大病,差點就把命丟在那座孤寂的寺院裏。要知道,那年的香林寺是沒有人的,僧侶們全讓破四舊的趕出了廟宇。若不是放羊的老羊倌,怕是……
鄧源森怒從心起,差點壹把火將寺廟燒掉。
秦繼舟的步子終於停在了龍鳳峽水庫面前。峽還是那個峽,兩山對峙,奇峰劍影。北邊的龍首山昂著驕傲的不曾屈服的頭顱,高高的兩個龍柱已不在,當年被他親手炸掉,當時還無比激動,覺得幹了件驚天地泣鬼神的事。龍眼處已是千瘡百孔,面目全非,但山的氣勢還在,這麽多年了,它的氣勢咋就壹點不減呢?緩緩轉過身來,南邊的鐵櫃山卻成了另番景色,滿目的綠已不再,茂盛的植被成了殘留在記憶中的美麗碎片,永遠不再復現。現在的鐵櫃山,樹沒了,灌木沒了,跟龍首山壹樣,光禿禿的,除了蒼涼,再就是粗鄙。是的,粗鄙。當山失掉靈色失掉水壹般的記憶後,除了粗鄙還能剩什麽?
壹座山在短短幾十年間從滿目翠綠變得慘不忍睹,除了無休止的砍伐,怕是河成了主要原因。每每看到這山的荒涼,秦繼舟就不由得這麽去想。有人說當年修水庫壞了龍脈,結果壹水庫的水沒養住壹座山,楞是把鐵櫃山的綠給沖沒了。秦繼舟不信。流域內已有不少山變成這樣了,毛藏草原都變得幹癟,變得枯瘦,何況缺雨少水的山。
水啊。秦繼舟長嘆壹聲,回過身去,目光怔怔地盯住了庫區。
這還能叫水庫嗎?兩山之間,窄閉的峽谷裏,壹座大壩孤獨地立著,奔騰的河已不在,咆哮的水已聽不見,眼前呈現的,是洗腳盆就能舀盡的壹汪可憐的臟水。兩只鴨子疲憊地走在樹皮壹樣幹裂的庫區裏,壹只斷了尾巴的黃狗邁著散淡而又乏力的步子,不時停下,沖天汪汪上幾聲。
天沒有回聲。
風也是靜止的,天空晴得沒有壹絲兒雲,整個山谷死壹般的寂,壓抑的能讓人背過氣去。
當年的火熱場面呢,人山人海那個陣勢呢?不是說人能勝天嗎,怎麽人讓天逼成了這個樣子?
秦繼舟久久地盯著庫區,盯著那座大壩。這座大壩對他這壹生,有著太多的牽連,太多太多的愛與恨。不只是愛情,絕不是,秦繼舟是壹個把愛情埋葬了的人,他知道愛情在某個人逃逸到寺廟的那壹刻,就已徹底死去,再也不可能復活。他這次來,是想搞明白壹個問題,這輩子,是不是真錯了,錯在哪裏。
錯在哪裏啊——
驀地,耳邊又響起地主五鬥的聲音:“人算啥,天又算啥,人不過是只蟲子,誰都可以踩死妳。天是網啊,鷹都沖不破,妳想?再者,人幹嗎要跟天鬥,人跟人鬥的還不狠嗎,還不狠嗎?還要跟天鬥,戰天鬥地,臨終,賬都要算到人頭上,算到人頭上啊——”
那時候,他跟地主五鬥已經很要好了,這要感謝路波,如果不是這個老右,那年他跟地主五鬥是搭不上話的,更別說幫他教他。路波起先對他是不屑的,壹個整天被槍押著被半瞎嘆牲口般喝嘆著的落魄男人居然敢對他不屑,這讓秦繼舟很不理解。可是有天夜裏他從窯洞裏翻出壹撂紙,用來寫認罪書的麻紙上繪著各種各樣的圖,細壹看,竟是在為大壩完善著設計。
倏忽間,秦繼舟就明白了,柳震山為什麽要把路波從別的地方押來,為什麽又將他跟地主五鬥關在壹個窯裏,原來是有目的的啊——
那是秦繼舟第壹次冷靜下來思考問題,也是秦繼舟第壹次從內心裏把自己隱掉,以仰視的姿態去打量別人。他感到了自己的無知、淺薄。他沖路波說:“失敬,失敬啊。”
路波懷疑地打量著他,不相信秦繼舟這樣的人會對別人表示出尊敬,當秦繼舟第二句話出來時,路波的眉頭松開了,心裏寬慰了壹下。
秦繼舟說:“我太自以為是了,現在我才明白……”明白什麽他沒說,或者他還沒完全明白過來,但這態度已經起了作用。路波友好地看著他說:“峽谷地質條件復雜,水流湍急,大壩必須安全,萬年大計,安全為本。”
秦繼舟又是壹震,換了他挨批挨鬥,怕是心裏斷然不會這麽想。壹個沒有仇恨的人!忽然間,他心虛了,近乎虔誠地看著路波,等待他後面的話。路波卻不再說什麽,捧起那些紙,低頭思考去了,不時拿出鉛筆,在圖上補充些什麽。秦繼舟傻站壹會,乖乖坐下來,眼神裏終於有了敬畏。
人對人的征服其實是瞬間的事,這點人比動物簡單,但人對人的敬仰卻是很漫長的壹個過程。此後若幹年,秦繼舟心裏便有了神。後來他們說到了放炮,路波還是堅持己見,壹再強調龍首山根本就不適合做料場,要求指揮部馬上將料場選到對面鐵櫃山上。
“想得美。”壹旁聽著的地主五鬥忽然插進了嘴。
“妳是巴望著多死幾個人吧?”路波毫不客氣地挖苦道。
“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有的人輕如鴻毛,有的人重若泰山,我是鴻毛。”地主五鬥壹邊拿針挑爛手上的血泡壹邊說。
路波斜他壹眼,慢悠悠說:“還是批的不夠,多挨幾繩子妳就老實了。”恰在這時,山上突然傳來壹聲響,壹股塵煙之後,那面讓人心驚的白旗又舉了起來。山下頓時啞巴。白旗跟死亡是連在壹起的,如果有人受傷,山上舉的是黑旗。
良久,兩個被改造的人擡起頭來,互視壹眼,路波帶著仇恨似的說:“又死壹個,妳打算裝多久?”
“我沒裝!”地主五鬥恨恨說。
“妳裝!”
“沒裝!”
“裝!”
“我沒!”地主五鬥突然跳出幾個蹦子,然後壹泄氣,像條死狗壹樣癱地上不動了。過了壹會,見秦繼舟傻呵呵地看著他,突然來了勁:“有本事妳上山啊,幹嗎要把他們糊弄上去?”
“我沒糊弄。”秦繼舟說。
“放屁,不是妳是誰,妳個吃五谷不拉人屎的,那是人命啊,六個,讓妳白白害掉六個,都還沒結婚呢,嗚嗚……”五鬥哭了起來。
“我真沒有。”秦繼舟還在狡辯,他不認為發動大家上山是鬧劇,他還是認為什麽艱難險阻都能戰勝,就看我們有沒有決心。這個被熱情沖昏頭腦的年輕人,那壹年的確是時而清醒時而糊塗的。
“妳是鬼,真想壹鐵鍁砍死妳!”地主五鬥恨恨說完這句,起身,孤獨地往河邊去了。路波點上煙,騰雲駕霧地抽。這天路波告訴秦繼舟,這個工地上幾千號人,真正能在龍首山放響炮的,怕就壹個五鬥。
“那就讓他上山啊,立功贖罪。”秦繼舟急不可待地說。
路波極其失望地剜他壹眼,慢吞吞道:“他沒罪,贖罪的應該是妳。”
這話讓秦繼舟全身壹陣痙攣,罪這個字,第壹次跟他掛上鉤。不過路波並沒放棄,兩天後他跟秦繼舟說:“想不想冒險?”秦繼舟不明就裏,他已經不敢在路波面前輕易說話表態了,說什麽也是錯誤,只好老老實實聽他把話講完。路波接著說:“妳可要想好,上去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他是批鬥對象,萬壹出事,他的命保不住。”
“沒這麽嚴重吧?”秦繼舟嚇得白了臉。
事實表明,那次如果不成功,他頂多被摘掉頭上的光環,對地主五鬥來說,卻是萬劫不復的深淵。所以跟著五鬥上了山,五鬥說什麽他都不敢犟嘴,老老實實按人家說的去做。
他大開了眼界啊。
在此之前,秦繼舟根本想不到放炮還有那麽多學問。大學裏沒學過,只是從相關書籍上看的。在他看來,放炮不過是壹項簡單勞動,膽大心細便可。那麽大壹座山,炸幾塊石頭還不容易?等到了山上,壹看,登時懵了。這哪是山,簡直就是狼牙!
地主五鬥先是帶他看了壹遍,凡是前面放過炮的地方,五鬥都看。看完就搖頭,就嘆息,就唉唉地嘆個沒完。後來說,反了反了,逆著放而不是順著放,全反了,怪不得呢。秦繼舟並不懂正與反,眼睛被血刺得生痛,幾乎不敢睜眼,有條胳膊還夾在石縫裏,沒拿出來。他居然認出了那條胳膊,是鄧家山大隊民兵五羊的,五羊是全工地發動後第五個報名的,家裏窮,跟同村的石榴好上了,石榴家不同意,嫌窮,五羊想立功,立了功石榴家就不能不同意了。誰知……
“過來!”秦繼舟還盯著五羊的半截胳膊發呆,五鬥厲聲喊他壹句,道:“上了山,心裏就甭再想別的,啥也看不見,知道不?”秦繼舟傻呵呵地點頭,五鬥指著面前的巖石說:“炮眼從西往東打就順了,再者不能挨這麽密,這夥狗日,壹口想吃個胖子,哪能打這麽密,不出事才怪。”說著,掏出懷裏錘子,開始敲點。
五鬥說:“先放兩個,不能急,試探壹下山性,山是急性子,妳就得是慢性子。山要是慢性子,妳急也無用。”
山有脾性。這是秦繼舟那年學到的又壹個知識,後來才知道,這不是知識,這怎麽能叫知識呢,這是活人的理啊。這話是地主五鬥說的,同樣的話地主五鬥還說過很多,他這才陸陸續續明白,不只是山,河也有脾性,路也有脾性,就連壹塊石頭,也保不準會有性子。萬物皆是,何況人乎?五鬥居然說了句文言文。這個五鬥啊。
五鬥壹前壹後打出兩個眼,把他叫跟前,如此這般講了壹通,然後讓他出去。秦繼舟不離開,五鬥火了:“有些東西能學,有些不能學,出去!”秦繼舟就怏怏不樂地出去了,站在了安全處,操作面上只剩了五鬥壹個。結果,那天的炮響了,成功極了。壹前壹後,兩聲過後,大片的石塊很講規則地落下來,壹塊也沒落在操作面上,全都乖乖地滾到了山下。山下雷鳴般地歡呼時,地主五鬥抹著頭上的汗說:“記住了,下去之後就說是妳放的,千萬甭提我。”
許多年後,秦繼舟才明白五鬥那麽做的用意。當年是堅決不許四類分子和右派成功的,所有的錯誤和失敗都可以歸到他們身上,成功卻不許沾半點。於是他再次成名,省報辟出半個版,專門介紹了他的事跡。
某種程度上說,是地主五鬥促成了他跟楚雅的婚姻,這個五鬥呀。
秦繼舟的腳步稍稍往前挪了挪,恍惚間,他又看到了地主五鬥,這個話不多,每說壹個字都能砸在別人心上的荒怪誕男人,真是折磨了他壹輩子,壹輩子啊。
那條斷了尾巴的狗跑過來,嗅嗅他褲角,想搖尾巴,又沒搖,抖抖身子,壹身亂毛就飛舞在了他褲管處。秦繼舟看見堤壩上走來壹人,是位老者,顫巍巍的。走近壹看,認出是水庫管理處的老張頭。
“秦教授啊,失敬失敬。”老張頭客氣著,拿腳踢了壹下黃狗,讓它規矩點,別亂舔客人褲子。老黃狗委屈地吐了下舌頭,傷感而笨拙地走了。秦繼舟說:“還沒退啊,以為妳早退下來了。”
“早就退下來了,家裏閑不住,又來了,現在不看水庫,看墳。”老張頭說。
“墳?”秦繼舟疑惑地問。
“嗯,是墳。塌了,老書記的墳進了水,老鼠在裏面造窩,跟縣裏匯報幾次,沒人管。五鬥墳裏去年還跑出壹窩兔子呢。這人,死了也不安閑的。”老張頭說著,引秦繼舟往堤壩北面庫管處院子裏去。秦繼舟腳步幾次停下,目光長長地伸過去,望住山腳下那片荒涼的塋地。
五鬥睡在那裏,老書記柳震山睡在那裏。當年死去的人,壹個也沒能回家,全都睡在那裏。
庫管處已經沒幾個人了,原來熱鬧的院子,現在怎麽看怎麽荒涼。值班的是位小姑娘,她不認得秦繼舟,所以秦繼舟的到來並沒帶給她什麽喜悅。她擡著目光,憂愁地望著天。老張頭跟她介紹了秦繼舟,說是省裏來的秦專家,當年這座水庫就是他指導著修的。姑娘鼻孔裏嗯了壹聲,又把目光伸向天空。她壹定是失戀了,或者就是在想,哪天才能離開這鬼地方,到縣城或者更好的地方去。玻璃窗戶裏探出幾雙眼睛,見是無關緊要的秦繼舟,又收了回去,並沒人出來歡迎。秦繼舟跟著老張頭進了房間,老張頭嘆說:“就這樣子了,妳全看到了,就這樣子了。”
夜裏,等老張頭睡下,秦繼舟壹個人摸索著出來,幽靈壹般往墳塋那邊去。每次到峽裏,這道功課總是少不了。有時是壹人去,默默地坐半個晚上,摸著黑挨個兒添把土。有時就那麽坐著,像是跟他們這夥人生氣,尤其五鬥,他怎麽能那麽早就死去呢,不是說要跟他當壹輩子夥計嗎,不是說要把女兒送到省裏讀大學嗎,還讓他親自教。怎麽就走了呢?
夜好濃,濃得化不開,心事也濃得化不開。老了,心事卻越來越重,年輕時活得多簡單,多直白,現在反而……
到了墳前,坐下,什麽也沒帶,空著手來。以前帶這帶那,來了就給他們,讓他們吃,讓他們抽,讓他們喝,可他們理都不理他,全都冷著臉,冷著臉啊。現在索性啥也不帶,空著手來,看看他們能咋?
先在老書記那坐了坐,想說啥,說不出,全堵在心裏。活著時沒覺得這人有多了不起,就是後來當了地委書記,也覺得沒啥了不起。對他總有意見,對他的建議老是排斥。關於這條河,關於這流域,他提過不少意見,可,算了,人都走了,還說什麽呢。不過現在,坐在老書記墳前,秦繼舟忽然就糊塗了,是自己過激,還是老書記保守?當年很多爭論,很多懷疑,怎麽就壹壹被老書記的話驗證。移民是他提出的,老書記反對過,可最終還是移了。上遊打井取水也是他提出的,老書記當年堅決反對,最終還是在政策的強壓下實施了。於是乎,龍鳳峽上遊,鄧家山甚至更上遊處,壹年就打出五十眼機井。水滾滾而來,下遊澆得那個滋潤喲。毛藏高原那邊,也未能幸免,當初老書記是堅決反對開采地下水的,是他,過高地估計了地下水藏量,提出了開發上遊,涵養下遊的理論,結果……
想著想著,他騰地站起來,跳到了五鬥這裏,罵:“五鬥妳說,妳說啊,真是我錯了嗎?”不等五鬥回答,他就捶起胸來。還用得著說嗎,事實擺在眼前,事實勝於雄辯啊。可他想不明白,自己咋能壹次又壹次地提出過激觀點呢,難道他對這條河,對這流域,真如老書記說的,沒有感情?
不,絕不!他相信,自己是有感情的,有啊。壹股淚滾下來,模糊了他的眼。怎麽能說沒感情呢,他覺得自己是把整個心融了進去,融了進去啊,怎麽就……再後來,他就越發痛悔得不行了,他壹次次地想起五鬥,想起那個狡黠詭異,愛耍點小聰明,心裏藏著不少小九九的家夥,那個人精。
他難過得要死了,五鬥的死,是他壹手造成的啊……
那年他終還是跟楚雅完了婚,鄧家英是失蹤了,可並沒阻攔住什麽。歷史的車輪真不可阻擋,這話放之四海皆準啊。指揮部破例騰給他們壹頂帳篷,做他們的新房。工地上破天荒開了壹壇子酒,他的丈人丈母娘都來了,笑嘻嘻地給大家敬酒,分發著喜糖,邊敬酒邊說些嚴格要求的話。後來在吳天亮和苗雨蘭面前停下,非常認真地說:“妳們也要加油啊,早日請我們吃喜糖。”吳天亮拉著臉沒說什麽,看得出他對這樣的祝福並不心存感謝,苗雨蘭卻已心花怒放,合不攏嘴地說:“多謝兩位首長,我們還想讓兩位首長當證婚人呢。”
“好啊。”楚雅母親說了壹聲,揚起目光,瞅了瞅天上的雲。“要下雨了。”她說。楚雅父親將目光從苗雨蘭身上挪開,裝模作樣也看了看天,點頭道:“是要下雨了,我們到指揮部去吧。”
雨果然劈劈啪啪下了起來。婚後第三天,大壩要合龍了,這是多麽激動人心的壹刻啊,苦戰兩年多,就等這壹刻。龍水河像是格外高興,忽然間水就漲了老高,超過了人們的預期。路波很緊張,吳天亮也很緊張,這樣高的水位,這樣急的水流,合龍是有危險的。吳天亮建議,要不再延緩幾天,等水位回到可控高度。馬永前擰起眉頭,不滿地教訓道:“什麽意思,又想退縮?”吳天亮不敢再建言了,這個時候的馬永前已很有權威,不久前龍山縣城爆發過壹場武鬥,造反派差點將柳震山揪出來,給他戴上牛鬼蛇神保護神的帽子。柳震山的腳步已經很少到工地,吳天亮的地位岌岌可危。
“秦大學妳說,這樣的水位合龍有沒有危險?”馬永前將話頭轉向秦繼舟,目光有點逼人。秦繼舟望著咆哮的河水,壹時無話,心裏也在不斷嘀咕。壹邊的楚雅急不可待替他回答:“報告首長,越是有危險,我們越是要向前。”
秦繼舟剛想拿眼瞪楚雅,馬永前說話了,馬永前的口氣很硬,他道:“聽到沒有,妳們還沒壹個女同誌有膽量。命令下去,各營做好準備,大壩按時合龍!”
“是!”壹直護衛在馬永前身邊的半瞎子雙腳啪地往跟前壹並,敬了壹個標準的禮,同時不滿地瞪了吳天亮壹眼,跑步走了。苗雨蘭情急地拽了壹下吳天亮,催促他快快表態。吳天亮卻把疑惑的目光投向秦繼舟,那目光裏有哀、有怨,更有擔憂。
秦繼舟佯裝看水位,將目光扭開。楚雅走過去,拉住苗雨蘭的手說:“不怕的,有我家繼舟在,根本不用擔心。”苗雨蘭壹扭身道:“怕不怕還說不定呢,光表態頂什麽用,得拿出實際行動來。”說完,臉上露出挑戰的表情來。
楚雅討了沒趣,有點求救似的將目光擱馬永前臉上,馬永前興高采烈說:“讓那些膽小之人看看,龍山人民壹定能創造奇跡。”
的確是奇跡。水位高過安全水位將近壹米,而大壩合龍留的口子又比設計寬出三米,這三米是故意留下的,目的就是為了奇跡誕生。各營早已準備好,就等總指揮馬永前壹聲令下。馬永前站在大壩最高處,身前身後都是荷槍實彈的民兵,仿佛他不是水庫工地總指揮,而是帶著百萬大軍,要沖破敵人封鎖線,直達會師地。十分鐘後,工地上響起壹聲槍響,大壩合龍開始了。
數百輛架子車拉著石頭,在各營營長的指揮下,爭先恐後往合龍處湧來。幾千號人不顧水深路滑,手拉著車,肩挑著筐,以排山倒海之勢,奮勇沖向大壩合龍處。這個時候是沒人敢猶豫的,那是壹場爭時間搶速度,具有高度組織性和紀律性的戰鬥,也是壹場人與自然的巔峰對決。秦繼舟和吳天亮各站在大壩豁口兩邊,手裏揮舞著紅、黃兩色指揮旗,兩位民兵替他們拿著小喇叭,喇叭裏傳出他們的叫喊聲。奇怪的是,兩個壹直暗暗較勁兒的技術人員,那壹刻思路是驚人的壹致,喊出的話都壹模壹樣。工地上的人更是心勁壹致,誰都鉚足了勁兒往豁口處投石頭,投草袋……
壹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三個,四個,終於,水流被截斷,兇猛的龍水河開始馴服,浪濤沖下來,在新起的圍堰上劇烈碰撞,濺出幾米高的水花,然後打個猛旋,呼嘯著往兩邊去了。秦繼舟和吳天亮臉上終於露出輕松,站在極高處的馬永前也松下眉頭,長長吐壹口氣,他可以提前慶賀勝利了。
哪知就在這壹刻,上遊突然沖下壹個浪,浪頭足有兩米高,像匹脫韁野馬,又像壹只怒獸,瘋狂地朝大壩沖來。吳天亮看見了,暗叫壹聲不好,秦繼舟也看見了,心裏連驚幾下。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浪已重重打在剛剛堆起的圍堤上。在邊上指揮的鄧源森大叫壹聲:“水要沖過去,快!”秦繼舟也下意識地喊了壹聲“快”。可是來不及了,那股不期而至的浪目空壹切地躍過剛起的堤壩,在眾人眼前跳幾個漂亮的舞步,放肆地沖向下遊。
水壹漫頂,意味著合龍失敗,千鈞壹發的關頭,壩上響起鄧源森的聲音:“跟我跳,造人壩!”
“造人壩!”不知是誰跟著呼應了壹聲,就見鄧源森壹個猛子躍下去,穩穩地站在了水裏。接著,堤壩上響起“撲通撲通”的聲音,人們扔了筐,扔了鍁,扔了架子車,壹個個跟著往下跳了。
那是多麽驚心動魄的壹幕啊,很多年後想起來,秦繼舟仍然感覺到心驚肉跳。那個時候,他腦子裏全亂了章法,根本就想不出應對之策,心裏只壹個聲音,完了,完了,徹底完了,前功盡棄啊,功虧壹簣!感嘆鄧源森魄力的同時,也暗自納悶,他怎麽就能想到用人體築壩呢?後來才知道,那是山裏人修水庫常用的壹種方法。沒有方法的時候,拿命賭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壹天,前後不到半小時,河裏跳進兩千號人,吳天亮下去了,秦繼舟下去了,鄧家英下得比他們還早,就連苗雨蘭,也情不自禁跳了下去。大壩上站著的楚雅目瞪口呆,她不敢跳啊,這可是拿命玩,她當然玩不起。她看看高處的馬永前,見人家雖然驚惶失措,卻無跳下去的意思,便也心安理得起來,不過很快,她就沖水裏喊了:“繼舟,秦繼舟,妳咋這麽糊塗啊。”
那天真是糊塗了,以後只要壹想起這事,秦繼舟就會這麽懺悔。他糊塗啊,他怎麽能跳下去呢。他不跳,水裏的人很有章法,他們都聽鄧源森的。他壹跳下去,下面立刻亂套。鄧源森沖他斷喝壹聲:“誰讓妳下來的,二柱,把他拖上去!”叫二柱的立刻掙紮著沖他過來,想把他提走,可是水太猛了,浪壹個接著壹個,咆哮聲淹沒著壹切。有人摔倒,爬起來,又摔倒。鄧源森大喊著:“抱住脖子,堵人墻!”人們就互相抱住脖子,像壹根鐵鏈子那樣串起來。秦繼舟也想做裏面壹個鏈,太想做了,於是掙紮著過去,想在人墻中間找自己的位置。鄧家英看見了他,從人墻中抽出身子,吃力地沖他喊:“到這邊來,秦……”後面的字沒說出來,鄧家英被壹個浪打翻,連站幾下,沒站起,嘩就越過了堤壩。
“家英!”
“家英!”水裏連著響起幾聲,第壹聲是秦繼舟喊的,第二聲是她爸鄧源森喊的。但是鄧源森並沒撲向女兒,他站的位置太重要了,壹旦松手,整個人壩就會倒掉。不知為什麽,秦繼舟忽然就明白,這個時候該他出手了,再不出手,怕有些事就再也沒了機會。於是他猛地壹躍,像個遊泳高手壹樣沖向鄧家英。
堤壩上響來撕心裂肺的壹聲:“不要,繼舟!”楚雅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水中那壹躍,她的聲音完全失真。隨後,她就發瘋似的往堤壩上跑了,她的哭聲在那壹天格外響亮。
秦繼舟根本就不會遊泳,這個北方大學的水文水資源教師,居然是個旱鴨子,水技實在糟糕得很。說的也是,那壹工地的人,又有幾個會遊泳呢?連嗆幾口水後,秦繼舟似乎站了起來,可是壹個浪沖過來,重重打翻他,秦繼舟被惡浪席卷著,狠狠地撞向壹塊石頭。隨後,他就什麽也不知道了。隱約記得,被浪打暈的那壹刻,他是喊過壹聲家英的,是的,他喊的是家英,而不是鄧家英,也不是小鄧!
“秦大學!”人墻裏突然傳來壹聲。誰也沒註意到地主五鬥啥時跳下水的,築人壩根本輪不上這些壞分子,他們沒有資格。他們跳下水,很有可能是搞破壞,所以事先馬永前再三叮囑,壹定要看管好這些壞分子,包括右派路波。
但是地主五鬥跳下了水,不但下來了,還結結實實成了人墻中的壹員。
眼見著秦繼舟像死去的魚壹樣肚子朝天被水卷下去,地主五鬥惡狠狠罵了句娘,壹個猛子紮過來就不見了。
那天的場景此後多年裏被人反復提起,但人們更多的把話頭集中到了吳天亮身上,因為那天的鄧家英是吳天亮救上岸的,不管苗雨蘭多麽傷心,多麽的不情願,這個事實卻被幾千號人看到了,而且經久不絕地傳誦著。關於地主五鬥,那年卻成了壹個禁忌,他救了秦繼舟不假,但此事被馬永前壹句話就否定了。
“他哪是救,他是想趁亂謀害。”
以後多年,再也沒人敢提五鬥,更不敢說是他救了秦大學。不敢說啊,說了,下場比五鬥更慘。但是,地主五鬥死了,被大水沖走了,人們只找到他壹只鞋,其他的,啥也沒了。
沒了。
葬在山下墓裏的,不是地主五鬥,是那只鞋。
路波流著淚說:“他拼盡最後壹絲力氣,才把妳推上岸,才把妳推上岸啊,這個五鬥。”
壹陣風吹來,卷起壹股子塵埃,風中夾雜著幾片落葉。風是黃風,整個世界瞬間也變成了黃色。
跪在五鬥墳前,秦繼舟眼裏哪還能止住淚。
他是壹個躲在記憶暗處的人。
每次踏上祁連,秦繼舟總要生出不少懺悔,這懺悔有時來得毫沒來由,卻又極其強烈,仿佛,流域變成這樣,是他壹手造成的。這是壹種非常可怕的感觸,但又抵擋不了,仿佛壹口深井,已把他牢牢困住。天旱得厲害,前些日子雖然降過壹場雨,但在秦繼舟眼裏,那不能叫雨,頂多是老天掉下幾個淚渣子。有雨的日子壹去不復返,很多日子都壹去不復返。人生就是這樣,老在懺悔中往前走,懺悔成了活著的理由。
這次出來,好像是生了老婆和兒子的氣,其實不,怎麽可能呢,如果生他們的氣,秦繼舟相信自己是活不到現在的。尤其老婆楚雅,他似乎已經習慣,愛鬧鬧去吧,他已沒有壹點反抗的欲望。
人是不能見啥也反抗的,反抗有時候是那麽的無濟於事。秦繼舟是動過離婚念頭的。他們的結合在當年來說是件挺轟動的事,水庫修壹半時,北方大學突然組織了學習團,到龍鳳峽等幾個水庫接受教育。楚雅興奮地來到龍鳳峽工地,見面就說:“我爸誇妳呢,幹得好棒。”
她爸那時是北方大學副書記,她媽更是不簡單,在省裏。秦繼舟在下面的壹應表現,都通過特殊渠道傳到他們夫婦耳朵裏,讓女兒到龍鳳峽工地,不能不說有某種目的。
這目的很快被挑到明處。秦繼舟因為成功攻破龍首山爆破難關,將全新的爆破辦法手把手教給工地爆破人員,壹時成了英雄,好多記者來到龍鳳峽,大力報道他的英雄事跡。很快,壹道嘉獎令頒了下來,給他親手戴上光榮花的,就是自己未來的嶽母,壹個漂亮得讓人咋舌的中年女人。此後不久,壹個落雨的夜晚,秦繼舟被請進谷水地委招待所,跟他談話的是楚雅的父母。他們說:“我們已決定把女兒嫁給妳了,有妳這樣壹個紅色樣板做我們的女婿,我們很高興。妳有什麽想法,可以說出來。”說完後,夫妻倆對望壹眼,等待他的回答。秦繼舟好不吃驚,那時候他腦子裏真是沒有結婚概念的,就連戀愛這樣的想法也不敢有,覺得是種恥辱。所有的人都在為社會主義建設奮鬥,都在鼓足幹勁,大幹快上,他怎麽能談情說愛呢?資產階級的東西萬萬要不得啊。可跟他談話的是組織,是……他垂下頭,半天不作聲。楚雅母親矜矜壹笑:“看來小秦是同意了,好吧,我們做父母的就不多說什麽了,妳們還有壹段時間,可以互相接觸壹下,增加革命感情嘛,時機成熟時,我們會通知妳,婚禮我們會抓緊張羅的。”
說完,夫婦倆就走了。秦繼舟還沒回過神來,就有兩撥人先後走進來,都是代表組織跟他談話,要他珍惜這機會,要他接受組織考驗,要他拿出滿腔熱情來,迎接挑戰。他們把愛情也說成是挑戰,口氣就跟要他赴湯蹈火壹樣。秦繼舟還能說什麽呢,那是壹個組織決定壹切的年代,個人在組織面前,除了響應和服從,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
有發言權的是楚雅。她突然做出壹個決定,留在龍鳳峽水庫不走了,要跟秦繼舟並肩戰鬥。戰鬥的結果就是在龍鳳峽水庫大壩將要合龍的前壹天,在水庫工地舉行了神聖的婚禮。
而在那壹天,水庫工地上同時發生壹件離奇事,鐵姑娘隊副隊長鄧家英失蹤了,派出去很多人都沒找到,她的父親鄧源森怒氣沖沖說:“姓秦的,妳真他媽不是東西,我女兒要有個三長兩短,我把妳丟河裏當沙洗!”
那壹刻,秦繼舟才恍然明白,這對父女這麽長時間裏對他隱藏了什麽。天啊,怎麽可能,怎麽可能嘛!他大張著嘴,吃驚地望著鄧源森。然後回過目光,盯住自己的準妻子。他的目光瞬間變得迷茫,變得恐懼而不安,不知所措。楚雅及時地說:“繼舟妳鎮定點,不就丟了壹個村姑,妳驚慌什麽?”又罵鄧源森:“這個男人好粗野,他有什麽權利教訓妳?這裏的人咋都這麽粗野啊——”
粗野的並不是別人,正是楚雅。這是婚後很久秦繼舟才明白過來的,可是晚矣。那時候他們已經有了兒子秦雨,在兒子秦雨之前,楚雅不小心還流過壹次產。當時龍鳳峽水庫大壩已經合龍,秦繼舟又熱情不減地去了南營水庫,懷孕的楚雅跟在他後面,誰勸也不回去。他們像壹對發了瘋的羊,認為只有修水庫的地方才有草。其實秦繼舟心裏明白,楚雅是怕他。那個時候楚雅已經知道鄧家英對他是怎麽回事了,工地上的人都在風言風語,說他們的鄧家英太傻了,人家秦大學怎麽會看上她呢?人家是省城來的,又是大學老師,後面還站著有權有勢的嶽父母,怎麽可能對壹個鄉下妹子動情呢?很快有人反駁,鄉下妹子咋了,鄉下妹子就不能喜歡別人?馬上又有人嘆:“能,咋不能呢,可喜歡了又能咋,差點把命搭上,喜歡不起啊。”
是差點把命搭上。
得知秦繼舟要跟楚雅結婚,要成為省裏來的楚雅的丈夫,鄧家英哭了幾夜,然後上了香林寺,她要到香林寺當尼姑。沒想到寺裏不久,害了壹場大病,差點就把命丟在那座孤寂的寺院裏。要知道,那年的香林寺是沒有人的,僧侶們全讓破四舊的趕出了廟宇。若不是放羊的老羊倌,怕是……
鄧源森怒從心起,差點壹把火將寺廟燒掉。
秦繼舟的步子終於停在了龍鳳峽水庫面前。峽還是那個峽,兩山對峙,奇峰劍影。北邊的龍首山昂著驕傲的不曾屈服的頭顱,高高的兩個龍柱已不在,當年被他親手炸掉,當時還無比激動,覺得幹了件驚天地泣鬼神的事。龍眼處已是千瘡百孔,面目全非,但山的氣勢還在,這麽多年了,它的氣勢咋就壹點不減呢?緩緩轉過身來,南邊的鐵櫃山卻成了另番景色,滿目的綠已不再,茂盛的植被成了殘留在記憶中的美麗碎片,永遠不再復現。現在的鐵櫃山,樹沒了,灌木沒了,跟龍首山壹樣,光禿禿的,除了蒼涼,再就是粗鄙。是的,粗鄙。當山失掉靈色失掉水壹般的記憶後,除了粗鄙還能剩什麽?
壹座山在短短幾十年間從滿目翠綠變得慘不忍睹,除了無休止的砍伐,怕是河成了主要原因。每每看到這山的荒涼,秦繼舟就不由得這麽去想。有人說當年修水庫壞了龍脈,結果壹水庫的水沒養住壹座山,楞是把鐵櫃山的綠給沖沒了。秦繼舟不信。流域內已有不少山變成這樣了,毛藏草原都變得幹癟,變得枯瘦,何況缺雨少水的山。
水啊。秦繼舟長嘆壹聲,回過身去,目光怔怔地盯住了庫區。
這還能叫水庫嗎?兩山之間,窄閉的峽谷裏,壹座大壩孤獨地立著,奔騰的河已不在,咆哮的水已聽不見,眼前呈現的,是洗腳盆就能舀盡的壹汪可憐的臟水。兩只鴨子疲憊地走在樹皮壹樣幹裂的庫區裏,壹只斷了尾巴的黃狗邁著散淡而又乏力的步子,不時停下,沖天汪汪上幾聲。
天沒有回聲。
風也是靜止的,天空晴得沒有壹絲兒雲,整個山谷死壹般的寂,壓抑的能讓人背過氣去。
當年的火熱場面呢,人山人海那個陣勢呢?不是說人能勝天嗎,怎麽人讓天逼成了這個樣子?
秦繼舟久久地盯著庫區,盯著那座大壩。這座大壩對他這壹生,有著太多的牽連,太多太多的愛與恨。不只是愛情,絕不是,秦繼舟是壹個把愛情埋葬了的人,他知道愛情在某個人逃逸到寺廟的那壹刻,就已徹底死去,再也不可能復活。他這次來,是想搞明白壹個問題,這輩子,是不是真錯了,錯在哪裏。
錯在哪裏啊——
驀地,耳邊又響起地主五鬥的聲音:“人算啥,天又算啥,人不過是只蟲子,誰都可以踩死妳。天是網啊,鷹都沖不破,妳想?再者,人幹嗎要跟天鬥,人跟人鬥的還不狠嗎,還不狠嗎?還要跟天鬥,戰天鬥地,臨終,賬都要算到人頭上,算到人頭上啊——”
那時候,他跟地主五鬥已經很要好了,這要感謝路波,如果不是這個老右,那年他跟地主五鬥是搭不上話的,更別說幫他教他。路波起先對他是不屑的,壹個整天被槍押著被半瞎嘆牲口般喝嘆著的落魄男人居然敢對他不屑,這讓秦繼舟很不理解。可是有天夜裏他從窯洞裏翻出壹撂紙,用來寫認罪書的麻紙上繪著各種各樣的圖,細壹看,竟是在為大壩完善著設計。
倏忽間,秦繼舟就明白了,柳震山為什麽要把路波從別的地方押來,為什麽又將他跟地主五鬥關在壹個窯裏,原來是有目的的啊——
那是秦繼舟第壹次冷靜下來思考問題,也是秦繼舟第壹次從內心裏把自己隱掉,以仰視的姿態去打量別人。他感到了自己的無知、淺薄。他沖路波說:“失敬,失敬啊。”
路波懷疑地打量著他,不相信秦繼舟這樣的人會對別人表示出尊敬,當秦繼舟第二句話出來時,路波的眉頭松開了,心裏寬慰了壹下。
秦繼舟說:“我太自以為是了,現在我才明白……”明白什麽他沒說,或者他還沒完全明白過來,但這態度已經起了作用。路波友好地看著他說:“峽谷地質條件復雜,水流湍急,大壩必須安全,萬年大計,安全為本。”
秦繼舟又是壹震,換了他挨批挨鬥,怕是心裏斷然不會這麽想。壹個沒有仇恨的人!忽然間,他心虛了,近乎虔誠地看著路波,等待他後面的話。路波卻不再說什麽,捧起那些紙,低頭思考去了,不時拿出鉛筆,在圖上補充些什麽。秦繼舟傻站壹會,乖乖坐下來,眼神裏終於有了敬畏。
人對人的征服其實是瞬間的事,這點人比動物簡單,但人對人的敬仰卻是很漫長的壹個過程。此後若幹年,秦繼舟心裏便有了神。後來他們說到了放炮,路波還是堅持己見,壹再強調龍首山根本就不適合做料場,要求指揮部馬上將料場選到對面鐵櫃山上。
“想得美。”壹旁聽著的地主五鬥忽然插進了嘴。
“妳是巴望著多死幾個人吧?”路波毫不客氣地挖苦道。
“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有的人輕如鴻毛,有的人重若泰山,我是鴻毛。”地主五鬥壹邊拿針挑爛手上的血泡壹邊說。
路波斜他壹眼,慢悠悠說:“還是批的不夠,多挨幾繩子妳就老實了。”恰在這時,山上突然傳來壹聲響,壹股塵煙之後,那面讓人心驚的白旗又舉了起來。山下頓時啞巴。白旗跟死亡是連在壹起的,如果有人受傷,山上舉的是黑旗。
良久,兩個被改造的人擡起頭來,互視壹眼,路波帶著仇恨似的說:“又死壹個,妳打算裝多久?”
“我沒裝!”地主五鬥恨恨說。
“妳裝!”
“沒裝!”
“裝!”
“我沒!”地主五鬥突然跳出幾個蹦子,然後壹泄氣,像條死狗壹樣癱地上不動了。過了壹會,見秦繼舟傻呵呵地看著他,突然來了勁:“有本事妳上山啊,幹嗎要把他們糊弄上去?”
“我沒糊弄。”秦繼舟說。
“放屁,不是妳是誰,妳個吃五谷不拉人屎的,那是人命啊,六個,讓妳白白害掉六個,都還沒結婚呢,嗚嗚……”五鬥哭了起來。
“我真沒有。”秦繼舟還在狡辯,他不認為發動大家上山是鬧劇,他還是認為什麽艱難險阻都能戰勝,就看我們有沒有決心。這個被熱情沖昏頭腦的年輕人,那壹年的確是時而清醒時而糊塗的。
“妳是鬼,真想壹鐵鍁砍死妳!”地主五鬥恨恨說完這句,起身,孤獨地往河邊去了。路波點上煙,騰雲駕霧地抽。這天路波告訴秦繼舟,這個工地上幾千號人,真正能在龍首山放響炮的,怕就壹個五鬥。
“那就讓他上山啊,立功贖罪。”秦繼舟急不可待地說。
路波極其失望地剜他壹眼,慢吞吞道:“他沒罪,贖罪的應該是妳。”
這話讓秦繼舟全身壹陣痙攣,罪這個字,第壹次跟他掛上鉤。不過路波並沒放棄,兩天後他跟秦繼舟說:“想不想冒險?”秦繼舟不明就裏,他已經不敢在路波面前輕易說話表態了,說什麽也是錯誤,只好老老實實聽他把話講完。路波接著說:“妳可要想好,上去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他是批鬥對象,萬壹出事,他的命保不住。”
“沒這麽嚴重吧?”秦繼舟嚇得白了臉。
事實表明,那次如果不成功,他頂多被摘掉頭上的光環,對地主五鬥來說,卻是萬劫不復的深淵。所以跟著五鬥上了山,五鬥說什麽他都不敢犟嘴,老老實實按人家說的去做。
他大開了眼界啊。
在此之前,秦繼舟根本想不到放炮還有那麽多學問。大學裏沒學過,只是從相關書籍上看的。在他看來,放炮不過是壹項簡單勞動,膽大心細便可。那麽大壹座山,炸幾塊石頭還不容易?等到了山上,壹看,登時懵了。這哪是山,簡直就是狼牙!
地主五鬥先是帶他看了壹遍,凡是前面放過炮的地方,五鬥都看。看完就搖頭,就嘆息,就唉唉地嘆個沒完。後來說,反了反了,逆著放而不是順著放,全反了,怪不得呢。秦繼舟並不懂正與反,眼睛被血刺得生痛,幾乎不敢睜眼,有條胳膊還夾在石縫裏,沒拿出來。他居然認出了那條胳膊,是鄧家山大隊民兵五羊的,五羊是全工地發動後第五個報名的,家裏窮,跟同村的石榴好上了,石榴家不同意,嫌窮,五羊想立功,立了功石榴家就不能不同意了。誰知……
“過來!”秦繼舟還盯著五羊的半截胳膊發呆,五鬥厲聲喊他壹句,道:“上了山,心裏就甭再想別的,啥也看不見,知道不?”秦繼舟傻呵呵地點頭,五鬥指著面前的巖石說:“炮眼從西往東打就順了,再者不能挨這麽密,這夥狗日,壹口想吃個胖子,哪能打這麽密,不出事才怪。”說著,掏出懷裏錘子,開始敲點。
五鬥說:“先放兩個,不能急,試探壹下山性,山是急性子,妳就得是慢性子。山要是慢性子,妳急也無用。”
山有脾性。這是秦繼舟那年學到的又壹個知識,後來才知道,這不是知識,這怎麽能叫知識呢,這是活人的理啊。這話是地主五鬥說的,同樣的話地主五鬥還說過很多,他這才陸陸續續明白,不只是山,河也有脾性,路也有脾性,就連壹塊石頭,也保不準會有性子。萬物皆是,何況人乎?五鬥居然說了句文言文。這個五鬥啊。
五鬥壹前壹後打出兩個眼,把他叫跟前,如此這般講了壹通,然後讓他出去。秦繼舟不離開,五鬥火了:“有些東西能學,有些不能學,出去!”秦繼舟就怏怏不樂地出去了,站在了安全處,操作面上只剩了五鬥壹個。結果,那天的炮響了,成功極了。壹前壹後,兩聲過後,大片的石塊很講規則地落下來,壹塊也沒落在操作面上,全都乖乖地滾到了山下。山下雷鳴般地歡呼時,地主五鬥抹著頭上的汗說:“記住了,下去之後就說是妳放的,千萬甭提我。”
許多年後,秦繼舟才明白五鬥那麽做的用意。當年是堅決不許四類分子和右派成功的,所有的錯誤和失敗都可以歸到他們身上,成功卻不許沾半點。於是他再次成名,省報辟出半個版,專門介紹了他的事跡。
某種程度上說,是地主五鬥促成了他跟楚雅的婚姻,這個五鬥呀。
秦繼舟的腳步稍稍往前挪了挪,恍惚間,他又看到了地主五鬥,這個話不多,每說壹個字都能砸在別人心上的荒怪誕男人,真是折磨了他壹輩子,壹輩子啊。
那條斷了尾巴的狗跑過來,嗅嗅他褲角,想搖尾巴,又沒搖,抖抖身子,壹身亂毛就飛舞在了他褲管處。秦繼舟看見堤壩上走來壹人,是位老者,顫巍巍的。走近壹看,認出是水庫管理處的老張頭。
“秦教授啊,失敬失敬。”老張頭客氣著,拿腳踢了壹下黃狗,讓它規矩點,別亂舔客人褲子。老黃狗委屈地吐了下舌頭,傷感而笨拙地走了。秦繼舟說:“還沒退啊,以為妳早退下來了。”
“早就退下來了,家裏閑不住,又來了,現在不看水庫,看墳。”老張頭說。
“墳?”秦繼舟疑惑地問。
“嗯,是墳。塌了,老書記的墳進了水,老鼠在裏面造窩,跟縣裏匯報幾次,沒人管。五鬥墳裏去年還跑出壹窩兔子呢。這人,死了也不安閑的。”老張頭說著,引秦繼舟往堤壩北面庫管處院子裏去。秦繼舟腳步幾次停下,目光長長地伸過去,望住山腳下那片荒涼的塋地。
五鬥睡在那裏,老書記柳震山睡在那裏。當年死去的人,壹個也沒能回家,全都睡在那裏。
庫管處已經沒幾個人了,原來熱鬧的院子,現在怎麽看怎麽荒涼。值班的是位小姑娘,她不認得秦繼舟,所以秦繼舟的到來並沒帶給她什麽喜悅。她擡著目光,憂愁地望著天。老張頭跟她介紹了秦繼舟,說是省裏來的秦專家,當年這座水庫就是他指導著修的。姑娘鼻孔裏嗯了壹聲,又把目光伸向天空。她壹定是失戀了,或者就是在想,哪天才能離開這鬼地方,到縣城或者更好的地方去。玻璃窗戶裏探出幾雙眼睛,見是無關緊要的秦繼舟,又收了回去,並沒人出來歡迎。秦繼舟跟著老張頭進了房間,老張頭嘆說:“就這樣子了,妳全看到了,就這樣子了。”
夜裏,等老張頭睡下,秦繼舟壹個人摸索著出來,幽靈壹般往墳塋那邊去。每次到峽裏,這道功課總是少不了。有時是壹人去,默默地坐半個晚上,摸著黑挨個兒添把土。有時就那麽坐著,像是跟他們這夥人生氣,尤其五鬥,他怎麽能那麽早就死去呢,不是說要跟他當壹輩子夥計嗎,不是說要把女兒送到省裏讀大學嗎,還讓他親自教。怎麽就走了呢?
夜好濃,濃得化不開,心事也濃得化不開。老了,心事卻越來越重,年輕時活得多簡單,多直白,現在反而……
到了墳前,坐下,什麽也沒帶,空著手來。以前帶這帶那,來了就給他們,讓他們吃,讓他們抽,讓他們喝,可他們理都不理他,全都冷著臉,冷著臉啊。現在索性啥也不帶,空著手來,看看他們能咋?
先在老書記那坐了坐,想說啥,說不出,全堵在心裏。活著時沒覺得這人有多了不起,就是後來當了地委書記,也覺得沒啥了不起。對他總有意見,對他的建議老是排斥。關於這條河,關於這流域,他提過不少意見,可,算了,人都走了,還說什麽呢。不過現在,坐在老書記墳前,秦繼舟忽然就糊塗了,是自己過激,還是老書記保守?當年很多爭論,很多懷疑,怎麽就壹壹被老書記的話驗證。移民是他提出的,老書記反對過,可最終還是移了。上遊打井取水也是他提出的,老書記當年堅決反對,最終還是在政策的強壓下實施了。於是乎,龍鳳峽上遊,鄧家山甚至更上遊處,壹年就打出五十眼機井。水滾滾而來,下遊澆得那個滋潤喲。毛藏高原那邊,也未能幸免,當初老書記是堅決反對開采地下水的,是他,過高地估計了地下水藏量,提出了開發上遊,涵養下遊的理論,結果……
想著想著,他騰地站起來,跳到了五鬥這裏,罵:“五鬥妳說,妳說啊,真是我錯了嗎?”不等五鬥回答,他就捶起胸來。還用得著說嗎,事實擺在眼前,事實勝於雄辯啊。可他想不明白,自己咋能壹次又壹次地提出過激觀點呢,難道他對這條河,對這流域,真如老書記說的,沒有感情?
不,絕不!他相信,自己是有感情的,有啊。壹股淚滾下來,模糊了他的眼。怎麽能說沒感情呢,他覺得自己是把整個心融了進去,融了進去啊,怎麽就……再後來,他就越發痛悔得不行了,他壹次次地想起五鬥,想起那個狡黠詭異,愛耍點小聰明,心裏藏著不少小九九的家夥,那個人精。
他難過得要死了,五鬥的死,是他壹手造成的啊……
那年他終還是跟楚雅完了婚,鄧家英是失蹤了,可並沒阻攔住什麽。歷史的車輪真不可阻擋,這話放之四海皆準啊。指揮部破例騰給他們壹頂帳篷,做他們的新房。工地上破天荒開了壹壇子酒,他的丈人丈母娘都來了,笑嘻嘻地給大家敬酒,分發著喜糖,邊敬酒邊說些嚴格要求的話。後來在吳天亮和苗雨蘭面前停下,非常認真地說:“妳們也要加油啊,早日請我們吃喜糖。”吳天亮拉著臉沒說什麽,看得出他對這樣的祝福並不心存感謝,苗雨蘭卻已心花怒放,合不攏嘴地說:“多謝兩位首長,我們還想讓兩位首長當證婚人呢。”
“好啊。”楚雅母親說了壹聲,揚起目光,瞅了瞅天上的雲。“要下雨了。”她說。楚雅父親將目光從苗雨蘭身上挪開,裝模作樣也看了看天,點頭道:“是要下雨了,我們到指揮部去吧。”
雨果然劈劈啪啪下了起來。婚後第三天,大壩要合龍了,這是多麽激動人心的壹刻啊,苦戰兩年多,就等這壹刻。龍水河像是格外高興,忽然間水就漲了老高,超過了人們的預期。路波很緊張,吳天亮也很緊張,這樣高的水位,這樣急的水流,合龍是有危險的。吳天亮建議,要不再延緩幾天,等水位回到可控高度。馬永前擰起眉頭,不滿地教訓道:“什麽意思,又想退縮?”吳天亮不敢再建言了,這個時候的馬永前已很有權威,不久前龍山縣城爆發過壹場武鬥,造反派差點將柳震山揪出來,給他戴上牛鬼蛇神保護神的帽子。柳震山的腳步已經很少到工地,吳天亮的地位岌岌可危。
“秦大學妳說,這樣的水位合龍有沒有危險?”馬永前將話頭轉向秦繼舟,目光有點逼人。秦繼舟望著咆哮的河水,壹時無話,心裏也在不斷嘀咕。壹邊的楚雅急不可待替他回答:“報告首長,越是有危險,我們越是要向前。”
秦繼舟剛想拿眼瞪楚雅,馬永前說話了,馬永前的口氣很硬,他道:“聽到沒有,妳們還沒壹個女同誌有膽量。命令下去,各營做好準備,大壩按時合龍!”
“是!”壹直護衛在馬永前身邊的半瞎子雙腳啪地往跟前壹並,敬了壹個標準的禮,同時不滿地瞪了吳天亮壹眼,跑步走了。苗雨蘭情急地拽了壹下吳天亮,催促他快快表態。吳天亮卻把疑惑的目光投向秦繼舟,那目光裏有哀、有怨,更有擔憂。
秦繼舟佯裝看水位,將目光扭開。楚雅走過去,拉住苗雨蘭的手說:“不怕的,有我家繼舟在,根本不用擔心。”苗雨蘭壹扭身道:“怕不怕還說不定呢,光表態頂什麽用,得拿出實際行動來。”說完,臉上露出挑戰的表情來。
楚雅討了沒趣,有點求救似的將目光擱馬永前臉上,馬永前興高采烈說:“讓那些膽小之人看看,龍山人民壹定能創造奇跡。”
的確是奇跡。水位高過安全水位將近壹米,而大壩合龍留的口子又比設計寬出三米,這三米是故意留下的,目的就是為了奇跡誕生。各營早已準備好,就等總指揮馬永前壹聲令下。馬永前站在大壩最高處,身前身後都是荷槍實彈的民兵,仿佛他不是水庫工地總指揮,而是帶著百萬大軍,要沖破敵人封鎖線,直達會師地。十分鐘後,工地上響起壹聲槍響,大壩合龍開始了。
數百輛架子車拉著石頭,在各營營長的指揮下,爭先恐後往合龍處湧來。幾千號人不顧水深路滑,手拉著車,肩挑著筐,以排山倒海之勢,奮勇沖向大壩合龍處。這個時候是沒人敢猶豫的,那是壹場爭時間搶速度,具有高度組織性和紀律性的戰鬥,也是壹場人與自然的巔峰對決。秦繼舟和吳天亮各站在大壩豁口兩邊,手裏揮舞著紅、黃兩色指揮旗,兩位民兵替他們拿著小喇叭,喇叭裏傳出他們的叫喊聲。奇怪的是,兩個壹直暗暗較勁兒的技術人員,那壹刻思路是驚人的壹致,喊出的話都壹模壹樣。工地上的人更是心勁壹致,誰都鉚足了勁兒往豁口處投石頭,投草袋……
壹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三個,四個,終於,水流被截斷,兇猛的龍水河開始馴服,浪濤沖下來,在新起的圍堰上劇烈碰撞,濺出幾米高的水花,然後打個猛旋,呼嘯著往兩邊去了。秦繼舟和吳天亮臉上終於露出輕松,站在極高處的馬永前也松下眉頭,長長吐壹口氣,他可以提前慶賀勝利了。
哪知就在這壹刻,上遊突然沖下壹個浪,浪頭足有兩米高,像匹脫韁野馬,又像壹只怒獸,瘋狂地朝大壩沖來。吳天亮看見了,暗叫壹聲不好,秦繼舟也看見了,心裏連驚幾下。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浪已重重打在剛剛堆起的圍堤上。在邊上指揮的鄧源森大叫壹聲:“水要沖過去,快!”秦繼舟也下意識地喊了壹聲“快”。可是來不及了,那股不期而至的浪目空壹切地躍過剛起的堤壩,在眾人眼前跳幾個漂亮的舞步,放肆地沖向下遊。
水壹漫頂,意味著合龍失敗,千鈞壹發的關頭,壩上響起鄧源森的聲音:“跟我跳,造人壩!”
“造人壩!”不知是誰跟著呼應了壹聲,就見鄧源森壹個猛子躍下去,穩穩地站在了水裏。接著,堤壩上響起“撲通撲通”的聲音,人們扔了筐,扔了鍁,扔了架子車,壹個個跟著往下跳了。
那是多麽驚心動魄的壹幕啊,很多年後想起來,秦繼舟仍然感覺到心驚肉跳。那個時候,他腦子裏全亂了章法,根本就想不出應對之策,心裏只壹個聲音,完了,完了,徹底完了,前功盡棄啊,功虧壹簣!感嘆鄧源森魄力的同時,也暗自納悶,他怎麽就能想到用人體築壩呢?後來才知道,那是山裏人修水庫常用的壹種方法。沒有方法的時候,拿命賭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壹天,前後不到半小時,河裏跳進兩千號人,吳天亮下去了,秦繼舟下去了,鄧家英下得比他們還早,就連苗雨蘭,也情不自禁跳了下去。大壩上站著的楚雅目瞪口呆,她不敢跳啊,這可是拿命玩,她當然玩不起。她看看高處的馬永前,見人家雖然驚惶失措,卻無跳下去的意思,便也心安理得起來,不過很快,她就沖水裏喊了:“繼舟,秦繼舟,妳咋這麽糊塗啊。”
那天真是糊塗了,以後只要壹想起這事,秦繼舟就會這麽懺悔。他糊塗啊,他怎麽能跳下去呢。他不跳,水裏的人很有章法,他們都聽鄧源森的。他壹跳下去,下面立刻亂套。鄧源森沖他斷喝壹聲:“誰讓妳下來的,二柱,把他拖上去!”叫二柱的立刻掙紮著沖他過來,想把他提走,可是水太猛了,浪壹個接著壹個,咆哮聲淹沒著壹切。有人摔倒,爬起來,又摔倒。鄧源森大喊著:“抱住脖子,堵人墻!”人們就互相抱住脖子,像壹根鐵鏈子那樣串起來。秦繼舟也想做裏面壹個鏈,太想做了,於是掙紮著過去,想在人墻中間找自己的位置。鄧家英看見了他,從人墻中抽出身子,吃力地沖他喊:“到這邊來,秦……”後面的字沒說出來,鄧家英被壹個浪打翻,連站幾下,沒站起,嘩就越過了堤壩。
“家英!”
“家英!”水裏連著響起幾聲,第壹聲是秦繼舟喊的,第二聲是她爸鄧源森喊的。但是鄧源森並沒撲向女兒,他站的位置太重要了,壹旦松手,整個人壩就會倒掉。不知為什麽,秦繼舟忽然就明白,這個時候該他出手了,再不出手,怕有些事就再也沒了機會。於是他猛地壹躍,像個遊泳高手壹樣沖向鄧家英。
堤壩上響來撕心裂肺的壹聲:“不要,繼舟!”楚雅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水中那壹躍,她的聲音完全失真。隨後,她就發瘋似的往堤壩上跑了,她的哭聲在那壹天格外響亮。
秦繼舟根本就不會遊泳,這個北方大學的水文水資源教師,居然是個旱鴨子,水技實在糟糕得很。說的也是,那壹工地的人,又有幾個會遊泳呢?連嗆幾口水後,秦繼舟似乎站了起來,可是壹個浪沖過來,重重打翻他,秦繼舟被惡浪席卷著,狠狠地撞向壹塊石頭。隨後,他就什麽也不知道了。隱約記得,被浪打暈的那壹刻,他是喊過壹聲家英的,是的,他喊的是家英,而不是鄧家英,也不是小鄧!
“秦大學!”人墻裏突然傳來壹聲。誰也沒註意到地主五鬥啥時跳下水的,築人壩根本輪不上這些壞分子,他們沒有資格。他們跳下水,很有可能是搞破壞,所以事先馬永前再三叮囑,壹定要看管好這些壞分子,包括右派路波。
但是地主五鬥跳下了水,不但下來了,還結結實實成了人墻中的壹員。
眼見著秦繼舟像死去的魚壹樣肚子朝天被水卷下去,地主五鬥惡狠狠罵了句娘,壹個猛子紮過來就不見了。
那天的場景此後多年裏被人反復提起,但人們更多的把話頭集中到了吳天亮身上,因為那天的鄧家英是吳天亮救上岸的,不管苗雨蘭多麽傷心,多麽的不情願,這個事實卻被幾千號人看到了,而且經久不絕地傳誦著。關於地主五鬥,那年卻成了壹個禁忌,他救了秦繼舟不假,但此事被馬永前壹句話就否定了。
“他哪是救,他是想趁亂謀害。”
以後多年,再也沒人敢提五鬥,更不敢說是他救了秦大學。不敢說啊,說了,下場比五鬥更慘。但是,地主五鬥死了,被大水沖走了,人們只找到他壹只鞋,其他的,啥也沒了。
沒了。
葬在山下墓裏的,不是地主五鬥,是那只鞋。
路波流著淚說:“他拼盡最後壹絲力氣,才把妳推上岸,才把妳推上岸啊,這個五鬥。”
壹陣風吹來,卷起壹股子塵埃,風中夾雜著幾片落葉。風是黃風,整個世界瞬間也變成了黃色。
跪在五鬥墳前,秦繼舟眼裏哪還能止住淚。